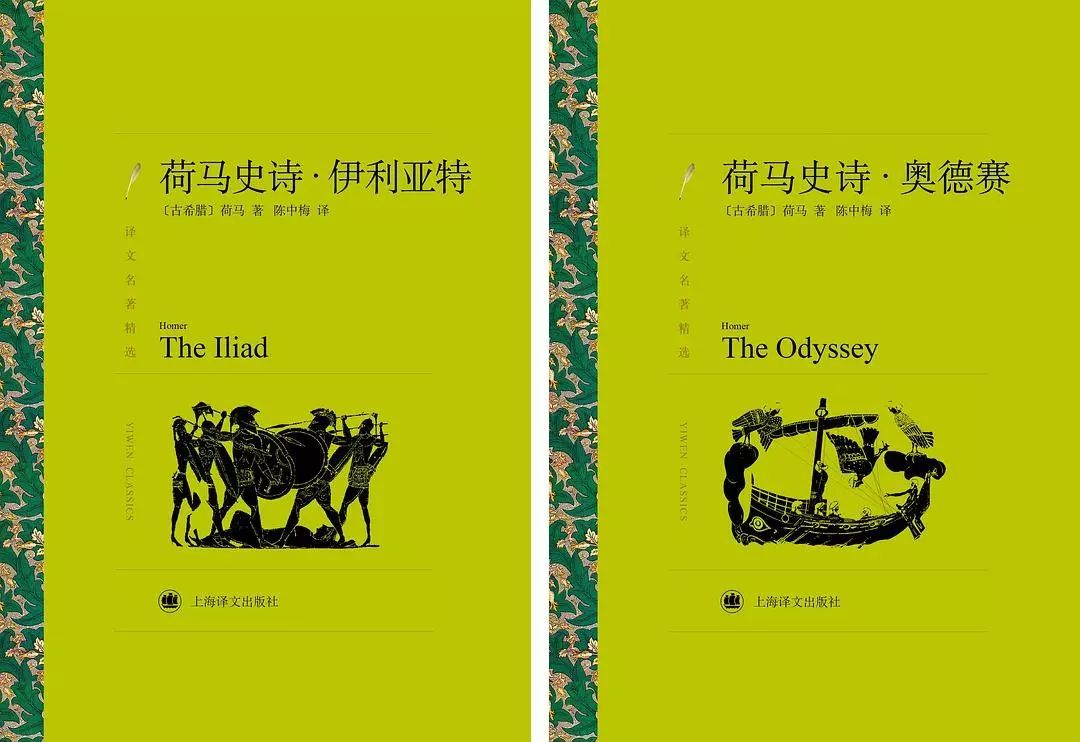王健,世界知名大提琴家。他四岁开始学习大提琴,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十岁的时候,他的个人演奏被拍摄进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之中,王健因此为世界上众多乐迷熟知,人们不吝称他为“大提琴神童”。
第 11 期:许知远对话王健 (精简版)
(以下对话编选自本期访谈)
音乐是我们灵魂传承的工具
许知远:阅读的兴趣是从小就有吗?
王健:对。比如在南大楼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小人书,《三国演义》《西游记》什么的,那时候也只有这些书看。
许知远:到耶鲁之后那些老师鼓励你们广泛阅读吗?
王健:其实专业老师倒没有提醒我们,只不过当时整个的文化风气是这样的。当时我的几个室友,一个研究神学,一个研究历史,跟这些人在一起,他们讲的一些事情会引起我的兴趣。而且我们学校的课程也是非常广泛的。后来我读完耶鲁大学,去茱莉亚音乐学院读书,在那里读的最多的是希腊史诗。譬如《荷马史诗》。其实你说学音乐读这个干什么?非常有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西方文化的起源,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在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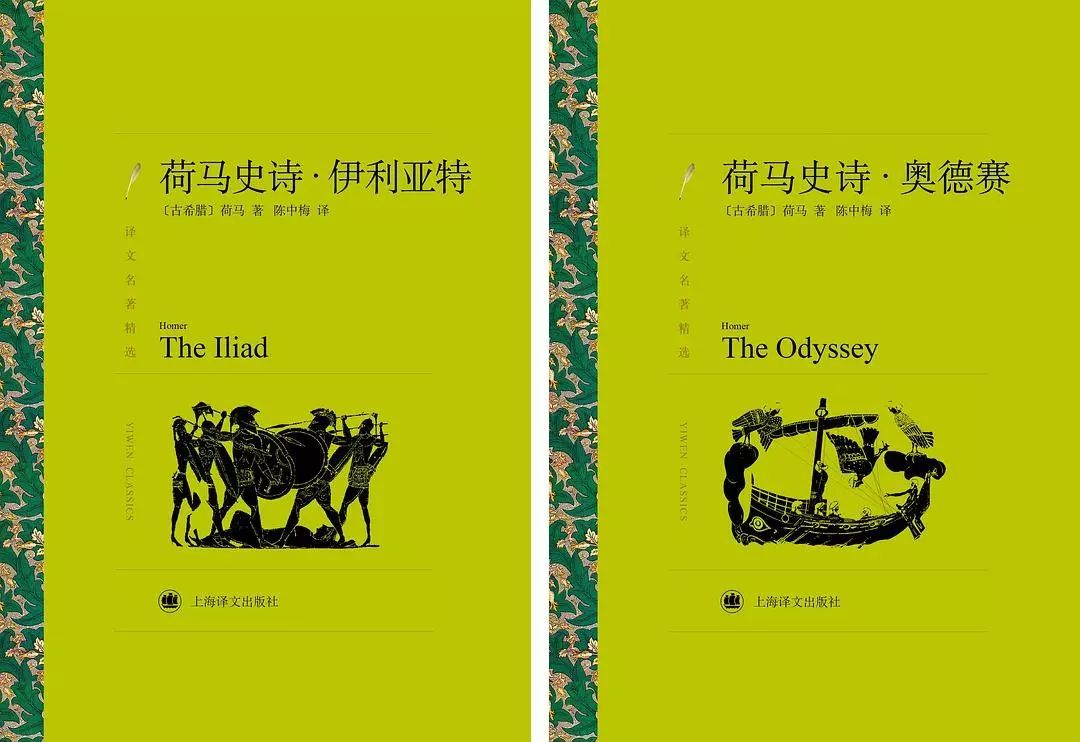
《荷马史诗》
[古希腊]荷马 著
陈中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
许知远:《荷马史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王健:里面那些英雄人物,面对死亡,勇敢地一步一步走过去。
许知远:而且是不断地离别。
王健:不断地离别,其中有一句话挺让人震撼的。斯巴达的一个士兵要出征,他的妈妈就拿着他家里祖传的一个盾牌跟她儿子说,儿子你要么把这个盾牌还给我,要么你就躺在这个上面回来。这种文化,它这种强悍的、坚定不拔的这种精神,非常令人震撼的,非常得壮,不光是悲,很壮。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王健
许知远: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着离别,这种疏离是不是对您的演奏有很直接的关系?
王健:这个绝对有。对人生离别的纠结、妥协或者抗衡,可以说是理解音乐里面那些比较深的情感的源泉。当然很多艺术其实到最后可能想妥协和解释的都是这个。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难、最不容易理解,可又是最不容易妥协的东西。这是人生最大的问题。
许知远:其实也是生命的主题。
王健:对,生命的主题。我们一直在逃避,一直不愿意想这个事情,但其实就是离别。随着你一天天长大,这个概念越来越强。你先想到的是你父母的离开,你朋友的离开,然后你想到自己离开,然后你想到你离开之后你的孩子会怎么样?谁都不愿意去想这种事情,但是问题是,这是不可逃避的一件事情,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预测的,只有死亡是必然会发生的。
我们当然要乐观,要以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音乐对这个有帮助。因为我听到这些音乐,你就觉得离别在你身边发生,或者说觉得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许知远:而且发生得比你还深沉。
王健:比你还深沉得多,比如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巴赫的作品。其实他们是永生的,不是吗?这是音乐最可贵的地方之一。音乐是灵魂的歌声,这些灵魂通过它的歌声永远生存在我们身边,我们每次演奏的时候,你听到就是他们的灵魂。从某种角度来说,音乐是我们灵魂传承的工具。
任何音乐最终的目的是反映人性
许知远:您去耶鲁、去大师班,老师们的演奏当时给您的震撼是什么?
王健: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拉法,但是他们都在讲自己的理念、在讲他们对人性的理解,或者是反映出他们自己人性中的东西,都很有个性。任何音乐最终的目的是反映人性,音乐本身其实并不重要,它只是个工具而已。如果你的音乐当中没有真正能够触发大家心灵中的振动的话,那音乐是没有意义的。
▲王健在耶鲁的老师,著名大提琴家 Aldo Parisot
许知远:您说每个演奏家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表达情感的主线,您是什么呢?
王健:我喜欢比较深刻的东西,所以我拉得比较好的是那些比较慢的东西,或者是情感特别深的东西。但是音乐不光是这个东西,音乐里也有欢快,也有希望,像马友友拉琴,他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他的音乐非常乐观、向上,他自己也是一种很阳光的性格:风趣、典雅,非常有格调。他可能属于一种绅士型的世界观,我则属于比较乡村式的世界观,是一个普通人的看法,但是我的音乐当中一些令人揪心的东西多一些。
▲马友友,知名大提琴家,曾获多次格莱美奖
许知远:那你觉得哪个作曲家跟你内心特别契合呢?
王健:其实都有,但是广义上来说,浪漫的作品里面会有更多这些东西。巴洛克音乐,或者早期的古典音乐描述的是天堂,典雅,尊贵,无忧无虑;浪漫的音乐,讲的是人间,在人间的人们想象天堂的样子,并期待去天堂——尽管也有美好,有期待,但是也有人间的揪心和挣扎。现代音乐描述的可能已经是想象回到人间的感觉了。
许知远:乌托邦已经没有了。
王健:更加揪心了。现代音乐讲的是更加令我们颤抖的一些情感。所以浪漫音乐最适合大提琴,因为它是一门很抒情的乐器。
一个演奏家必须要有一颗很灵敏的心
许知远:去理解一两百年前的作曲家,去理解他们的感受、心境,那些历史背景重要吗?
王健:当然重要,比如说演奏巴赫、海顿的作品,你必须了解当时这些音乐是干什么的。海顿或者莫扎特的音乐,绝大多数是宫廷音乐,或者是贵族们来给客人们搞娱乐的,所以这种音乐必须有它的华贵,尊贵,和与世无争。比如浪漫作品,如埃尔加,为什么他会有那么深切的悲伤在里面?了解这些会对你有帮助,但是这个绝对是辅助性的。
▲由王健演奏的 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专辑封面
有两种理念一直在争论:感性重要还是理性重要?我向来认为,理性是总结感性的工作,感性永远走在理性之前,我坚信人类的感性其实是我们灵魂的指明灯,理性只不过是帮助我们,让感性往更深的地方去发展。有些东西我们不理解,但是能感觉得到,为什么你听到一些音乐就有感觉?为什么这几个音组合起来你就觉得好听?音乐里面很有可能包含了一些方程式,只不过我们的大脑还算不出来,但是我们感觉得到这个方程式。所以说我只有对这个作品有很强大的感受以后,我才能把它演奏得好,面对一个作品,我如果不起鸡皮疙瘩,没有兴奋在,我不可能拉好它——再有知识,再有理念,对历史再有研究,也没有用。音乐终究是个感性的东西,没有感觉的人是不能搞艺术的,他再聪明也没用。
▲摄影师:高远
但是相反很多人,他很笨,没有什么知识,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但他就是有感觉,他就能搞艺术,只不过可能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因为这些人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去丰富自己,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有感觉,没有感觉的人,即便把所有的音乐理论背下来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许知远:对,这种感觉是需要拓展和加深的,对此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式吗?
王健:一个演奏家必须要有一颗很灵敏的心,灵敏到在各种不同的事物中能感受到一些东西。这个没法教,但是我会提示学生们,要把宏观放得大一些,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会跟学生说,“你现在讲的是你自己的故事,拉得不错,但是你能不能想象一下,现在你站得远一点,去讲别人的故事?”这个已经离得远一点了,更宏观大一点了,然后我会让他再想得大一点,去讲身边很多朋友的故事。到最后我会跟他说,“你要想象这个作品,假设上帝创造了人类,可是祂忘记了我们,自己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把我们遗忘在原地,让我们自生自灭。几十亿年之后,祂终于回来了,祂说在这地球上,我以前好像造过这些人,可怎么没了?全没了?然后祂听到了我们的音乐,里面有这样的演奏,有这样的人:我们人类挣扎过,我们快乐过,我们努力过,我们追求过,终于,祂替我们落泪了。”
我经常这样去提示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站得更远。如果只讲自己的故事的话,别人会不接受,或者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可站得远一点就会让人觉得这就是人类的故事——全人类到最后说不定都会没有的。在这个情况下,有些事情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另外一些事情则非常重要。
许知远:那真实的人生体验呢?比如说20世纪很多重要的作曲家,包括演奏家,他们卷入到时代的巨大变迁之中,甚至目睹各种悲剧的发生。但其实您的个人经历是很顺利的,您会遗憾缺乏那样的一种经历吗?
▲肖斯塔科维奇,前苏联著名作曲家,在与前苏联政府的关系中,他既受到过政权的褒奖,也与其有过冲突
王健:我最爱看的书是历史书,这个可能会对我的人生观有改变。看了很多历史的话,对动荡和变迁还是有感觉的,虽然我自身没有经历过,但是可以想象得到人生有多么不易。你说得对,一般是在很动荡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去经过多大的苦难磨炼,如果你有一颗比较敏感的心,你能感受到这些事情。有人问过我最讨厌什么?我想了半天,其实没有什么不太能容忍的,我唯一不能容忍、完全不能接受的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哪怕这个人再优秀,再伟大,如果这个人没有同情心,我会觉得他的心是冷的,我会很讨厌这个人,我会根本看不起他。当然有些人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你知道他其实还是有同情心的,这个人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同情心可能是人心中最重要一点,不是吗?它让我们人类可以互相理解。
音乐超出了具体的个案,
它是一个总结,而不是一个叙事
许知远:同情心其实也是某种抗议,某种宣言,它意味着要为弱者表达某种声音,或者说是被淹没的声音。
王健:其实音乐没有那么具体,它更升华了。音乐超出了具体的个案,它是一个总结,而不是一个叙事;它要描述的是一个理解,是一件事情发生以后的回忆;它不是在讲某件事情,而是讲这件事情以后的事情。
许知远:“理解”作为一个立场重要吗?
王健:立场很重要,但是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还是我说的,有些事情你站在某个角度是有对错的,再往后退一步,对错就变得模糊了,再往后退,就不一定有对错了,再往后退,就无关紧要了。
许知远:那会不会陷入某种相对主义?或者说陷入一种好像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状况?
王健:是的,一切都可以理解。你说我们人生这些恩怨,从宇宙的角度来说,不可以理解吗?太能理解了,这都是无所谓的。
许知远:当然世界不是黑和白的关系,但是某种意义上还是有颜色差别的,还是有黑和白的分别的,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白就变成黑了吧?
王健:对,所以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正义感至关重要,它是一颗善良之心的必然产物。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的音乐是不一样的,他有骨气在里头,这我是听得出来的;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能量去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这我也能听得出来。
▲摄影师:高远
许知远:那我一直蛮好奇的,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德国军官们也都听贝多芬,但是他们同时可以做出特别糟糕的事情来,作为一个音乐家,看到这样的例子是什么感觉呢?
王健:人心是很复杂的。我们任何人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会干出很坏的事情来,你必须接受这一点,人心就是这样。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做文天祥,你别忘了,我们之所以崇拜这种人,就是因为他们是怪人,他们是不正常的人。绝大多数人,我不知道你,我是绝对做不了文天祥的。可也正是如此,我非常看重他,这种人太少有了。对于人类来说,哪怕他再有正义感,再能分辨对错,在涉及到个人利益之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妥协,这就是人性。但是这些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在正义的一面。所以说要创造一个正义的环境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要求所有人做文天祥,这是不可能的。你说的这些德国军官,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在犯罪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选择去参与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不坚强,他们不是文天祥,可如果在一个环境下,给予他们一个机会,说,“我们可以反对希特勒”,我想他们大多数人会的,只要他们看到有成功的希望。
▲讲述纳粹政府与音乐天才莫扎特关系的著作《莫扎特与纳粹》
许知远:对,后面的问题一直也挺困扰我的,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审美和他的价值判断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能好多人都会说,一个读狄更斯的人可能比不读狄更斯的人更少犯错,或者更可能成为一个好人。
王健:你读这些书肯定会给你带来影响、启发,但这些启发只不过是点燃了你心中本来就有的东西,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到而已。但是如果内心不同意的话,他再说也是没有用的。这些书可以改变大家,但是它让我们更加理解自己,让我们有更加深度的人生观,而不是说彻底改变你——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人性很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