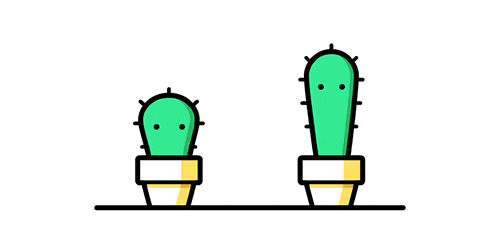“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
文 | 颜坤琰
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这段友情虽然短暂,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更显真挚。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今八一路雨田大厦的位置)、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协”)、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著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北中国》是戴望舒为萧红编发的最后一篇小说,有趣的是,此篇与他为萧红编发的第一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主题相同,情节上也有类似之处。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调同样浸透了浓烈的故园情怀,但《北中国》却写得更精致、细腻。小说于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于《星座》第901号至917号上。
戴望舒一直热情地关心着萧红他们,他担心他们不适应南国的生活,不时前往尖沙咀看望他们。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中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随着萧红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便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萧红是香港文协会员,戴望舒是香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萧红与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着较深的友谊,因此,在萧红病重之际及离世以后,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戴望舒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从杜宣的回忆录中可读到,戴望舒当时是积极参与其事的。杜宣在《忆望舒》中写道:“日军投降后,我是第一批进入香港的……望舒告诉我,萧红逝世时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杜宣说的这几个朋友中,就有戴望舒,还有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更是20世纪的“正气歌”。
5月,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冯亦代写道:“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尽管身体垮了,哮喘病更严重了,戴望舒却一直惦记着萧红。待身体稍稍恢复,他便让叶灵凤陪着去凭吊萧红。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腊月,他不顾病痛缠身,在朔风中艰难地步行六七个小时才来到浅水湾,这是何等真挚的友情啊!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写道:“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当时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9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了戴望舒一首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时,注明日期为1944年8月20日,这大概是他的写作日期。
一年后,戴望舒又来到浅水湾,想必是给萧红报告抗战胜利的喜讯吧!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杜宣在《忆望舒》一文中回忆道:“9月下旬,一个台风刚刮过的下午,望舒带着新波、紫秋和我去浅水湾……我们在浅水湾原来游泳场的沙滩上,看到了一丘孤坟,坟头上插了一个木签,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字……她是鲁迅先生亲自培养出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于此,只看到一抔黄沙,面对着无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愤交加。望舒说,当时出于无奈,只能将她葬在这里。”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戴望舒对萧红的怀念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他三年多无数次地去浅水湾扫墓祭奠,还在于他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写道:“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该诗全文如下: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情感真挚,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是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在漫漫黑夜,诗人在等待,萧红在等待,等待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是戴望舒从抗战初期升腾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深化和发展。学者王文彬说:“这首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伟大的诗篇。”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9期
责编 | 李唐
图片 | 网络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