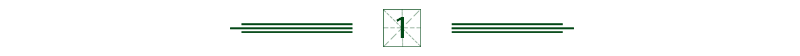妹妹的心跳越来越弱,当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慢慢变为直线,机器发出“滴……”的长鸣,我感到浑身冰冷,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那一刹那,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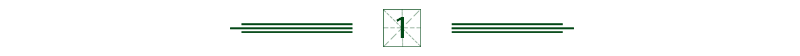
父亲最后一次见到我的三叔,是在1940年。
那年清明,山东青岛莱西老家被日本人占领,父亲就读的学校挂起狗皮膏药旗。眼看日军动不动就杀人放火,17岁的父亲纵然满腔怒火,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天,国家派往胶东沦陷区的教育指导员悄悄来到学校,劝说学生们去大后方:“青年学生都爱国,爱国就不能在日寇的刺刀下做亡国奴,到大后方去!”在鼓动下,父亲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决定到大后方求学。
悄悄离开的那天清晨,奶奶摸黑爬起来做手擀面为儿子送行,那是家乡的习俗,远行的人一定要吃了面才能出发。年仅9岁的三叔特地跑到外面折了柳枝,放在大哥手里。那也是祖宗传下来的习俗:亲朋好友一旦分离,送行者总要折柳赠给远行者,寓含“惜别怀远”之意。
在家人不舍的目光中,父亲毅然走出家门,一直不敢回头。全家老小就站在大门外,目送父亲离开,直到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晨雾中。
当年的祖屋至今还在
行至沂蒙山区,遇到日机轰炸,慌乱中,父亲跑进一块玉米地。待飞机飞走后,父亲走出玉米地,大声呼喊同学的名字,听到的却是老乡呼儿唤女的声音,他就这样与同学走散了,只能独自流亡。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沿路乞讨。夜里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在路旁或村头草垛里露宿,天亮后再接着赶路。
父亲将“战区流亡学生证”藏在衣服的夹缝里,混在逃难的老乡中,小心翼翼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一路迂回南下,来到安徽宿县。在牧师生熙安的帮助下,1940年冬父亲自宿县经蒙城、利辛到达阜阳。后来,他考入李先洲将军创办的国立二十二中。
多年后父亲回忆说:“开学第一节课,我是屏住呼吸听课,在艰难的抗战岁月,流亡生活虽然清苦,但能读书就是天堂般的日子。”
1944年9月,因日寇占领了豫、鄂一带的平汉铁路,父亲和他的同学再一次踏上流亡征途。途径河南省汝南县韩庄镇时,他的11位同学被突然追来的日寇杀害,最小的只有14岁。父亲因为走在前又跑得快,才躲过一劫。待日本人走后,父亲和同学找来当地老乡帮助挖土坑,才将11名同学一一埋葬,现场学生无不号啕大哭。
跨过平汉铁路,便是“水旱蝗汤”肆虐的中原大地。在河南泌阳县大河屯镇,父亲亲眼目睹这样一个情景:
一个已经咽气的妇女,坐靠在街边土墙上,臂弯里搂着个女婴,那孩子俯身贴在妈妈敞开的怀里,已经失去血色的嘴唇,还含着妈妈干瘪的乳头。
看到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女同学都背过身去掩面哭泣。父亲和几个男同学将这一对母女平放在墙边的地上后,不敢再多看一眼,默默走开了。
那年11月,父亲和他的同学脚蹬龙须草编成的草鞋,一路逆汉江西上,流亡到陕西的安康、汉阴和汉中一带继续求学。
在汉阴,父亲终于有机会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报平安,那时候,他已经离家流亡整整四年。
1948年初,还在求学的父亲收到我二姑写来的信:“大哥:三哥早在1946年就参军了,至今杳无音讯。”
父亲大吃一惊:15岁的少年,怎么就参军了呢?待看完信,才知原委。
原来,1946年秋天,八路军来到三叔就读的学校,游说学生参军。正在读初中的三叔在鼓动下,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胶东八路军警备四旅八团,当晚就丢下书包跟着八路军走了,甚至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只让同村的一位同学帮转告:“帮俺告诉俺妈姆(方言:妈妈),俺去当兵了。”当时一起走的还有同村的五个学生。
三叔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我奶奶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得直跺脚,爷爷只是坐在墙角埋头抽旱烟袋锅,一声不吭。
1949年底,贺龙的部队解放汉中,已参加工作的父亲转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野战军第十八集团军担任文化指导员。他多番打听三叔的下落,但一直没有消息。
1950年春节前夕,27岁的父亲转业,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做了一名教师。
爷爷奶奶喜极而泣。奶奶踱着三寸金莲,颤巍巍地从怀里拿出一封信,那是1949年底三叔给家里写回的第一封家书:
父母亲大人在上,这些年儿对不住你们,等打完仗,一定回来孝顺父母大人……儿现在一切均好,勿念……
凭着这封家书的地址,父亲终于和十年未见的弟弟取得了联系,那时,三叔驻守在浙江金山卫。不久,父亲收到三叔的第二封家书,从信中,父亲才得知了三叔离家后的经历。
在参加八路军扫清胶东日伪顽残余势力后,三叔跟随部队参加多次战役,包括胶东保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因作战勇敢,还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渡江战役中,三叔所在的二十七军八十师是全军中最早打过长江的部队,三叔也是全军第一批成功渡江的战士。
多年后,父亲坐在老家院子的一棵古桐树下,向我一句句背出当年三叔写回的家书:
我们一开始是隐蔽渡江,江面上船只密密麻麻,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救生圈是用芦苇做成的。船刚过江心,对岸的敌人发觉了,随即响起劈天盖地的枪炮声,我们一边拼命还击一边拼命划船,潮水般向长江南岸冲去。
……
“你三叔描绘的那场面比电影震撼多了。”父亲告诉我,渡江战役胜利后,八十师奉命参加了上海战役。部队攻击进入上海市中心后,立即担负起外滩和南京路一带的警卫任务。
夜间,八十师从师长、政委到每一个士兵,都一律打开背包,或席地而睡,或靠墙而眠,已是八十师二四零团团部卫生班班长的三叔,也奉命带领全班战士夜宿在繁华的南京路街头。
解放军夜宿南京路
那时,父亲已从国立二十二中毕业,并在陕西南郑县政府工作,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人民解放军露宿上海南京路街头的新闻照片,但他却不知当时三叔就驻守在南京路。
1950年10月底,父亲收到三叔的第三封家书,他在信中说:
朱总司令来部队做动员报告了,由此判断,部队不日就要北上开赴朝鲜,与“美国鬼子”作战。先不要告诉父母大人,切记。
父亲立即给三叔复信,因不见回音,又接连书信数封,却封封石沉大海。
收到三叔那封信后,全家一直都很揪心,原以为打完内战,三叔很快就会回家团聚,谁想到抗美援朝又开始了。
后来,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已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三叔所在部队也在当年11月开赴朝鲜。
全家只能在煎熬中苦苦等待。我的奶奶常常在村口大树下,一坐几个小时,呆呆看着远方,期盼小儿子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眼前。
1953年夏天,父亲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得知,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结束。那时候,已有志愿军陆续回国,全家四处打听三叔的下落,却一直没有音讯。
父亲心中隐隐有不详的预感,但后来看到报纸说,中国志愿军有大批人留在朝鲜,帮助朝鲜战后重建。他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奶奶,全家心中再度燃起希望。奶奶坚定地说:“宽儿(三叔小名)一定是在帮助朝鲜人民盖房子哩。”
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车辚辚马萧萧,最可爱的人回来了”的新闻。
父亲拿着报纸跑回家,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爷爷奶奶。
“要回来了,宽儿要回来了……”奶奶激动地不停念叨着,想方设法找来最好的面粉,她要给儿子做饺子接风。
这一年的3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布撤军公报,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3月16日是撤军回国的第一批。但一直等到10月25日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出朝鲜回国,三叔依然没有消息。
家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压抑,吃饭时,大家都很少说话。
这年冬天,一位邻村的志愿军战士复员回家,当年,他是与三叔一同参军的。父亲闻讯后,立即跑去找他了解情况。
那战士支支吾吾半天,终于告诉父亲:“我听说你三弟早在入朝鲜当年的东线战役中就牺牲了,但我和他不在一个部队,也没有亲眼看到。”
坚强的父亲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仍感到浑身冰凉,一下瘫坐在椅子里,半晌说不出话。
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父亲并未将这个消息告知二老,只谎称那名战士并不知情。
1958年年底,家里忽然来了两名县政府干部,手里拿着一张烈士证,上面,是三叔的名字。
65岁的爷爷不认字,当听清自己的小儿子牺牲的消息后,他表现得不像当时报纸上那些烈士父母一样坚强伟大,而是抄起身边的一把铁锨,向两名干部挥去,追得两名县干部满街跑。边追边骂:“俺儿都死这么长时间了,恁这才吭声?靳嫩个妈姆(山东俚语),还俺的儿子。”
一时间,村里的人都赶来围观,但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大家都沉默地看着,不久,我的几个婶婶开始低声啜泣。
村里人都知道,爷爷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参军,大儿子(父亲)早年流亡抗日,几次死里逃生,两个女婿在解放前也参军抗日。如今,最小的儿子又牺牲在朝鲜战场。
当父亲闻讯赶回家时,奶奶的一只眼睛已经哭瞎了,她虚弱地躺在炕上,一遍遍喊着三叔的小名:“我的宽儿啊,宽啊…….”空洞的眼里,已经没有泪水。
爷爷仍心气难消,对大儿子说:“恁说说,嫩兄(你弟)都死多长时间了,县里才吭声?”
父亲将爷爷拉到一边,悄悄告诉爷爷:“抗美援朝牺牲的人多了,您不知道,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都牺牲了。”
爷爷听到这话儿一怔,埋头抽起他的旱烟袋锅,不再吭声了。
1959年春节,大年二十九的上午,正在帮奶奶忙年饭的母亲听见院门口响起锣鼓和口号声,出门一看,是村里来送“光荣烈属”牌匾的拥军队伍。
在锣鼓和口号声中,看着拥军队伍将木质红漆、烫着金字的“光荣烈属”牌匾挂在自家门上,爷爷满脸自豪,奶奶昏花的眼里却溢满了泪水。
同样的牌匾在村里一共挂了五家人,当年村里和三叔一起去当兵的五个学生,最后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才知道三叔牺牲在朝鲜的事。
有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给英烈献花,回家后,父亲一脸凝重地告诉我:“你的三叔也是烈士!”
我吃惊地看着父亲说:“三叔的墓在哪里,我要去给他献花。”
“他牺牲在朝鲜,但不知道葬在哪里……”说完,父亲沉默了。
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父亲总要向我提起自己的这个弟弟,在他的描述中,三叔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他是孙家长得最英俊的男孩,浓眉大眼,活泼好动,从小好打抱不平,常常替被欺负的同学出头,学习非常好。
在老家院子的那棵古桐树下,父亲总是说着说着就陷入了沉默,眼睛里写满忧伤。
每次,都要重复强调一句:“不能忘了你三叔,他是英雄。”
母亲清晰地记得,父亲有一个印着“烟台地区优秀教师”字样的笔记本,里面夹着三叔写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那上面的字迹,潇洒极了。
家里挂上牌匾后,爷爷常常在院子里练功,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他又在练功,便拍手称赞,爷爷慢慢吐出一口气,说:“你三叔的功夫练得才厉害!”那是爷爷唯一一次主动向我提起三叔。
我后来在爷爷的老屋见过三叔的两张画像,那是家人请人画的。三叔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15岁离家参军时,还是个没长开的孩子,家人只有请来他生前的战友,根据战友回忆,让画师画出他参军后的模样。
多年后,那两张画像仍牢牢印刻在我心底:一张是头戴大檐帽的半身像,一张是骑着高头骏马,血气方刚,威风凛凛。
爷爷八十多岁的时候,逢人便会提及自己的小儿子:“俺儿子小宽,是烈士。”
我知道,三叔一直活在家人的心里。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与母亲聊起过去,她忽然对我说:“写写你三叔吧,你父亲生前最挂念的就是这个弟弟,六十多年了,不知他怎么死的,也不知葬在何处……”
我一阵心酸。寻找三叔的过往,就此埋进心底。
经过多番查找,终于在莱西市民政局找到了三叔的档案,我又通过翻阅志愿军二十七军八十师军史,才还原了三叔牺牲的经过。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原本作为攻台主力的二十七军,随即奉命由浙江开赴山东泰安地区整训。
11月1日,三叔随部队自泰安火车站乘闷罐军列北上,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于11月4日夜由安东(今辽宁丹东)乘火车进入朝鲜。入朝前,所有官兵按照命令一律摘下帽徽、领章等各种记号,并上缴所有随身印信和文件,就连毛巾上的“华东军区”的字样也被剪掉,更别说向家人写信了。
入朝后,二十七军原计划是围歼西线的英军二十七旅,后因敌军南退,而东线美军继续北犯,威胁西线志愿军的侧翼,于是,二十七军又奉命撤回安东,北上吉林临江再次入朝。在冰天雪地里,三叔和他的战友徒步300多公里,开进到东线战役的指定位置长津湖一带。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零下40度。而那年,是当地50年不遇的严冬。
11月24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第八、第十集团军对中朝军队发动第二次进攻。美军第七步兵师一个加强团的特遣队孤军深入,先期占领长津湖附近的新兴里和内洞峙村。
志愿军参战部队是二十七军八十师的3个团和八十一师的1个团。11月27日午夜,志愿军冒着鹅毛大雪向美军发起攻击。三叔所在的二四零团负责进攻新兴里西侧的内洞峙村,内洞峙易守难攻,双方战斗极为惨烈。美军隐蔽在地沟里,火力十分密集。起初以为是一个连的敌人,一打发现是一个营,敌人的坦克围成一个圈,手榴弹砸上去像是挠痒痒,不起任何作用。
战至28日,二四零团就减员达三分之二以上。二四零团一营,战前的编制是800余人,打完内洞峙后,只剩下了70余人。
到了28日夜,二四零团团长于春圃组织部队对内洞峙的美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但用钢铁武装起来的美军给冲锋的志愿军很大杀伤,原本就减员三分之二的二四零团兵力严重不足。关键时刻,于春圃命令团部的警卫班、卫生班、炊事班和通讯班也参加战斗(三叔那时是团部卫生班班长)。
一声令下,三叔和战友们冒死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小炸药包和六零炮弹等轮番炸向敌营。战斗到29日拂晓,内洞峙的美军五十七炮兵营被歼灭,美军的步兵营也被击溃逃到新兴里。就在这次战斗中,年仅19岁的三叔牺牲了。
经过5天4夜,这场血战终于结束。
多年后,时任美军第七步兵师五十七炮兵营营长卡罗·D·曾顿斯中校回忆:“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战斗,在二战中,我遇到过德军最后一次大反攻,但也不似长津湖(新兴里)之战这样激烈,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军的飞机大炮,而是零下40多度的严寒。入朝前,第九兵团的战士们大多穿着单薄。
二十七军官兵穿的是华东温带地区的过冬棉衣,衣里只装有一斤半的棉花,因冻死冻伤的减员远远超过了战斗减员。二四零团五连冲锋时受到美军炮火压制,全连迅即呈战斗队形卧倒,最后全部在雪地上渐渐“凝固”。
《三八线》剧照
负责防守死鹰岭的六连,在第二天战斗打响后却没有开火,兄弟部队派了一名参谋去了解情况,在阵地上,这名参谋看到战士们有的手持步枪面对坚守的山口,有的举着手榴弹随时准备投出,但一个个都无声无息,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们已经全部冻死,成了“冰雕”。
在长津湖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一共出现了三个冰雕连,除了上述五连、六连外,还有二连。其中,六连和二连全体指战员都牺牲了,五连有一个通讯员和一个病号,当时没有在阵地上,得以幸存。
有统计显示,在当年的那场战役中,志愿军九兵团冻伤3万多人,冻死四千余人。其中,九兵团的主力二十七军战斗伤亡八千余人,冻伤一万余人。很多战士还没投入战斗就被活活冻死。
美军一位叫里兹伯格的团长战后回忆:当他们执行撤退命令时,小心翼翼爬上山头,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积雪覆盖的堑壕之中是一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有百十号人,都据枪而待,枪口全都指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将要经过的地方。
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没有大衣,多数人还戴着单帽、穿着单鞋。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寒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密集的细小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
中国的志愿军战士,即便冻死,也没有放弃阵地,放弃执行自己的作战命令!
里兹伯格团长感叹:“这就是与他们鏖战了20多天的中国军队,这是些什么人啊?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为什么如此顽强,为什么具备着这样非同寻常的意志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现场的美军士兵,在里兹伯格的命令下,向志愿军战士的遗体敬了军礼。
1952年9月,第九兵团奉命从朝鲜回国,行至鸭绿江边,时任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下车,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宋时轮抬起头来时,警卫员发现,这位满头花白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
宋时轮
含泪看完这段悲壮的历史,我掩卷陷入沉思,忽然想起父亲曾坐在老家院子的那棵桐树下告诉我:“1958年复员回家的那个战士说,你三叔是被美军飞机扔下的炮弹击中的,他的脸一半没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说这话时脸上痛苦的表情。
而这痛苦,我直到2014年才真正深切体会到——那年妹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得知她离世的刹那,我感到浑身冰冷,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总有一天,我会去朝鲜长津湖畔柳潭里烈士陵园祭奠我的三叔,那里刻着他的名字:孙铭祥。那个陵园,长眠着二十七军8000多名官兵,但愿英雄的母亲们,永远都不知道战争残酷的真相。
三叔的网上虚拟纪念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