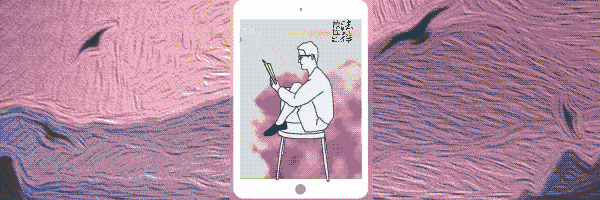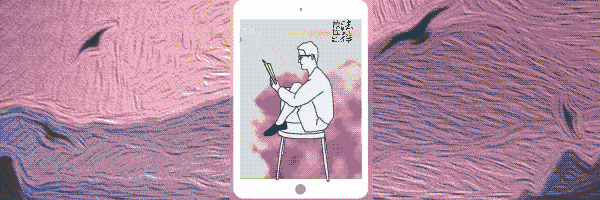
不知不觉,「法治周末」十大法治图书的评选,也成为了一种传统。传统意味着既成定势,意味着重章复奏。很多年后再回首每一年出版界、学术界选出的“十大法治图书”,也许会发现某种固有偏好和特定轨迹。
每年十本书,十年也不过百本。不知届时,哪些仍然是闪亮的名字,而哪些已被人们遗忘——其实这并不是坏事,或许这意味着今天人们痛苦的挣扎,已成为那时可有可无的笑谈——鲁迅就曾盼着自己的文字能够“速朽”,其意大抵如此。
年近中年的你,听腻了“现代转型”吗
有些作者亦已是“十大”的常客。一年前,李贵连教授的「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屈居次席;而今年,他凭借「1902:中国法的转型」终登榜首。
李贵连/著 312页/2018年10月
一方面可喜可贺,另一方面,大不韪地说一句,我们多希望,有关“西风东渐和中体西用”“拥抱变化和现代转型”这些字眼,能够被今日的年轻人所遗忘。
这些“95”后、“00”后年轻的法律人,本该轻装上阵,不用再背负过往;本该身穿精致的律师服,精雕细琢地建构商业规范和刑辩规则。
按照20年前我们学习法律时的预期,时至今日,他们的法律世界,早该没有这些“苦难记忆”“痛定思痛”和“百废待兴”。
他们早该像其他“95”后、“00”后那样,不知粮票、肉票长什么模样,听那个时代的穷困痛苦,如听天方夜谭般哑然失笑。
可惜的是,情况未及预期。今年我们的榜单中,仍然有「1902:中国法的转型」和「现代性的磨难:20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1901—1937)」,有呼吁以法律改革夺回租界审判权的「王世杰文集」,和似乎站在反面的「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冤案昭雪」和「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徐小群/著 411页/2018年8月
长期研究中西方法律交流 其实是单向交流 的李贵连教授在「1902:中国法的转型」中说,西方法、现代法的输入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到20世纪初期,已经经历一个甲子。
然而,20世纪初的法律改革者手中持有的,仍然是“很破旧、很浅薄、很粗糙”的“唯一能使用的新式武器”。
以那些武器试着革新旧制,其难度可以想象。
将徐小群的「现代性的磨难」和陆永棣的「落日残照」放在一起看,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徐小群想知道,“那些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如何俘虏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者,并推动他们根据这个观念来行动”,并且使他们甘受接连不断的挫折和磨难。其实答案就在「落日残照」和含冤的无数杨乃武案中。
陆永棣/著 342页/2018年6月
陆永棣说:“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目睹那些永远不会被载入刑部结案报告的屈打成招,那些失控的法内用刑与恣意的法外滥刑——假如回到那个时刻,也许任何人都会被“现代性话语所俘虏”。
而另外两本,也几乎逃脱不开这样的底色。
近代法律人王世杰每篇每章,都在陈述如何“以西法改造旧法”,以求收回租界审判权。有意思的是,在去年的榜单中,入选的是「钱端升全集」;今年轮到了一时瑜亮、当年合著「比较宪法」的王世杰。
王世杰/著 1408页/2017年12月
苏力的「大国宪制」看似在论述传统制度有其正当理性,但他每一句辩驳的背景,其实都是现代法对旧时法的批评反思——说得过分一些,其实是冷漠无视。
旧调重弹,听得津津有味,未尝不是一种悲哀。
苏力/著 624页/2017年11月
在 2019 年,我们还在讲现代性,还在努力讨论这样宏大的话语,并且感到艰辛和动摇,并且铭记起一百年前的前辈们,实在不是件光荣的事。
有时,我们以为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不过是原地绕了一个圈。
单从本次榜单来看,或许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路,还有些长。
启蒙这件事,梁任公、沈家本、王世杰、钱端升···这些前辈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同样逃脱不开。
既然没能拥有“天真无知”的权利,那么也只好不再逃脱。那些未竟的事,接过来继续便是,否则,何以寄希望于未来,更无以消遣无聊余生。
打开的窗户,不只是温柔的眼眸
因为个人工作的缘故,近年对外汇关心不少。外汇管理局某位领导曾说过一句令人心安的话:“我们不会重回资本管制的老路,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
不过,今年的榜单和往年相比,虽然仍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但无论是入选数量还是所涉主题,都显得稍微单薄一些。
当然,这绝不是说「温柔的正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和「美国法律史」的份量不够。只不过,相比法治周末首届十大图书评比那一年,似乎确实有些不同。
那是 2013 年,那一年共有四部“舶来之作”。于是我们抱怨,怎么经过如此多年的法治建设,我们仍然这样离不开西方样本。
琳达·赫什曼/著 408页/2018年3月
那年入选的四部“舶来之作”,分别是「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我们人民:奠基」和「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
这些主题,无论是美国宪法、联邦法院大法官、民主或是税收与法治的关系,都称得上经典隽永,并构成了现代法律文明的部分基石。
不过,对于“言必称西方”,当年的我们并不以为然。反而抱怨“我们对欧美世界具体的部门法、法律技术和法学创见,似乎不够感兴趣”,而只是盲目地套用那些宏大语词,沉迷其中。
“看云时觉得很近,看人时觉得很远”。这句话可以说得更直白些,随便找个法学院学生,他都能就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侃侃而谈,给你讲出宪法、民主、法治这些大词;可是你问他,美国证券法关于内幕交易是如何打击,或是美国专利法对于芯片设计是如何保护,恐怕他能说出来的还是只有这些大词。
这样的“西方样本”,恐怕也只有“温暖人心”的作用。
但是,这绝不是在说,此次入选的「温柔的正义」和「美国法律史」只不过是“洋鸡汤”。相反,它们比起那些大词横行的“洋先生”可爱得多,因为它们具体而微、关注细节,甚至不厌其烦地引用有关就业歧视、性骚扰、侵权认定、财产归属的法条。
「温柔的正义」讲述了美国第一位和第二位最高法院女法官的个人轶事,但更多地讨论了她们主审的经典判决。
「美国法律史」一书中,则充斥着有关公司治理、侵权归责的规则发展历史——虽然这本书的英文名称是“The law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上的法律,但并没有沉迷于讲述法治精神、民主理念如何引领美国人民。
施瓦茨/著 377页/2018年5月
相反,在作者施瓦茨看来,正是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起诉、和解和判决,那些数以万计的法庭辩论和含恨妥协,才真正形成了美国法律发展的历程,真正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
该如何理解才好呢?让我们听严复当年怎么说。这也是有关法律图书出版的一点掌故。
1909 年,严复翻译的「法意」 即「论法的精神」第七分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此,该书第一个中文版本终于出齐,完整地呈现在国人面前。「法意」全书还包括严复所加的 167 条按语,共五十多万言,从 1904 年起陆续分册出版,前后耗时五六年。
其中在卷十一「论自由法律之关于宪典者」中,严复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按语:“忧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 即当时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 ,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其端在此一事,说得很是明白。
书斋立法: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假如让苏力教授参加法治建设,制定民法典、刑法总则,他很可能会有些苦恼。
一方面,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宪制或是不成文的规则,都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是有其合理性的“公共产品”。要修改当前的立法,不是在质疑这种合理性吗?
另一方面,要制定新的规则,就需要弄清楚当前这个领域内的社会现状和发展方向,制定可能具有一点超前性、但不能超前的太多的规则。如果不能明确判断发展趋势,那最有可能的选择,或许是尽量忠于当下。
可是这样的立法,是不是又有些太保守了呢?
边界在哪儿,度如何把握,真的并不容易。然而,就有人在做这样不容易的制度建设工作。
本次榜单中,有关部门法的理论和实践占据了三分之一,分别是「我与刑法七十年」「民法总则通义」和「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高铭暄/口述 281页/2018年6月
刑法、民法这些看上去呆板无趣的字眼,其实也是由许多和你我一样真实的人在写就的。
高铭暄回忆起立法时最痛心的事时说:“自 1954 年 10 月刑法立法工作开始以来···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大修改稿 33 篇,还有无数改动较小的稿子,这些是立法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切,我都认真保存,按先后顺序装订成册,所有材料摞起来的高度大概有一米多···军宣队的人查验到这堆材料,问了问来源和存放者,随便翻了翻就说,这是没用的垃圾,直接拿去烧掉。当天,这些材料连同其他垃圾集中在一处,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听到这一消息,我心都凉了半截,怔怔地发呆。”
而参与了 20 余年民法典起草工作的孙宪忠则相对幸运,不但保留整理了民法典起草以来的立法笔记,还得以将其出版。这本「民法典立法笔记」中包含了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所提的十余项议案,以及二十余项人大代表立法建议和立法报告。
孙宪忠/著 569页/2018年6月
孙宪忠曾写过一首小诗,说“法典千年事,仓促铸大错”,所以宁愿做好充足准备,“磨刀不误砍柴功”。
而另一位民法学家郭明瑞的「民法总则通义」中,看上去更为理论的那些讨论,包括民法典该采取什么篇章结构、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编、知识产权法应否入典、要不要制定债法总则、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如何适用···正是这样的立法准备,事实上也影响、甚至主导着立法的方向。
郭明瑞/著 393页/2018年1月
有人说,那这不成了“教授立法”吗?然而,这有什么奇怪呢?法律从来不是垄断在“立法官员”手中,而是需要学界提供研究和养料。
假如我们进一步问,学界在参与立法时,提供什么样的支撑呢?如果问苏力,他或许会说,无非两样,一是洋办法,二是土情况。
教授们像掌握了拉丁文的僧侣,能够通过“打开的窗户”看到西方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办法。与此同时,教授们能够发动学生们,进行田野调查和街头调研,向立法机关提供“中国特色”。
理论上说,这两项工作如果都能做得好,学界将可以在法治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不过,理想照进现实,总有不少路要走。书斋就是书斋,不是庙堂也不是江湖。靠学者牵头,拿一部立法草案,怎么看像是游击队的打法,而不像是正规军的套路。然而,在某些领域内,教授们又确实是当仁不让的专家。也许,这也是我们正走在“现代性”之路上的表现。又应了那句老话:“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说句不中听的话,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样的局面也会进入博物馆,并被未来的人们所遗忘——这确实是一种遗憾,不过,对于学者们而言,或许也是一种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