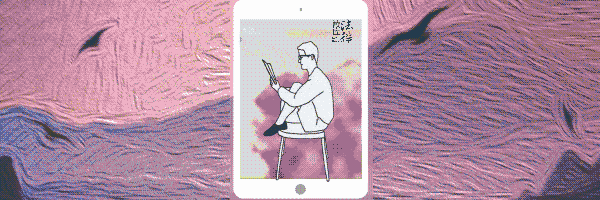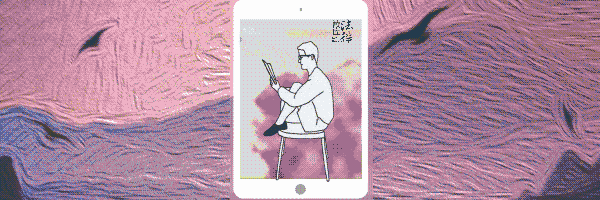
“山东公安”微信公众号3月24日发布通报称,对“聊城主任医师开假药”问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公安厅指导聊城市、东昌府区两级公安机关依法开展侦查调查,现已查清主要事实。
3月24日,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依法对陈宗祥、王清伟作出终止侦查的决定。
一、“假药”罪的衍变
据“山东公安”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2018年4月14日,患者王某禹因患小细胞肺癌和膀胱癌,入住聊城市肿瘤医院,同年11月10日因病去世。治疗期间,主任医师陈宗祥向王某禹之女王某青推荐未经批准的进口药“卡博替尼”,并让其自行购买。王某青请求陈宗祥介绍购买渠道,陈宗祥将购买过此药的病人家属王清伟介绍给王某青。应王某青之弟王某光请求,王清伟将为其父购买但未使用的1瓶“卡博替尼”转卖给王某光;后应王某光请求,王清伟又从段某真处帮其购买一瓶“卡博替尼”,共获利784元。
“卡博替尼”是由美国Exelixis生物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型分子靶向药物,对多种癌症广泛有效,被称为靶向药中的“万金油”。目前“卡博替尼”尚未被国内引进,属于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患者大多只能通过代购或其他方式购买印度版“卡博替尼”。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论处。根据该项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便是“假药”,“卡博替尼”符合《药品管理法》关于“假药”的认定。
这项“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按假药论处”的规定,源于2001年《药品管理法》的修订。2001年之前的《药品管理法》所规定的“假药”并不包含此种情形。生产、销售假药罪,是《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罪名。对于“假药”的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依照的是《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根据上述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规制的“假药”与《药品管理法》规制的“假药”是在同一意义上进行使用的。
但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前,《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未必就可以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
主要原因在于,1997年《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生产、销售的“假药”必须“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才会被认定为1997年《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未经批准的进口药品虽是“假药”,但进口药品常常因具有医学上的疗效,也就不会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进而难以被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
问题发生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加大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的力度,1997年《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被删除。修改后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罪状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生产、销售假药罪不断扩张,犯罪打击范围因此扩大。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假药”与《药品管理法》的“假药”具有同一性,曾经被未被认定为“假药”罪的进口药,因属于“假药”重新被“入罪”。
类似于“我不是药神”案件(原型陆勇案)不断进入司法程序,备受社会关注。时隔三年之后的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药品解释》),明确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免责事由,“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药品解释》的出台,将部分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假药案”出罪,在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之间架起桥梁,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假药”罪的认定。
二、情理与法律的碰撞
据媒体报道,中国是癌症大国,全球20%的新发癌症病人在中国,24%的癌症死亡病人在中国,肝癌患者的新发率、死亡率甚至达到50%。癌症患者在抗癌路上的不易,不断涌上媒体,被称为“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想活着的人”。癌症患者群体的求生欲,催生了一批批为患者代购“假药”的销售者。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改变,虽然有效打击了不具有药效的“假药”制售行为,但也将未经批准进口药的代购行为认定为犯罪。正是这种现实情况,令癌症患者们不解的是,“帮助病友的人”为何被认定为犯罪。
从法律上来说,有偿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药,必然是违反《药品管理法》,进而触犯生产、销售假药罪。
然而,要注意的是,销售“不假假药”的行为,不同于销售没有医学疗效的假药。这种行为虽触犯了《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扰乱了国家药品管理秩序,但基于销售行为同时具有救死扶伤的性质,客观上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挽救和延续了患者的生命,实质上具有某种救助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类似于“紧急避险”(为了保护较大利益,不得已损害较小利益)的救助行为。
为此,多数刑法学者为限缩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犯罪圈,不断作出努力,比如以实质危害限缩假药的认定,以卖方立场限缩销售行为,以行政法与刑法二分法加以限制假药等等方面。
司法现实是,《药品管理法》对于“假药”的认定无法被推翻,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药也就会被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正是由于生产、销售假药罪以及《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学者们上述种种努力终难以被司法者认可。因此,《药品解释》的规定也就成为“假药”销售者的救命规定,不少类似案件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要么不作为犯罪处理,要么定罪免刑或判处缓刑。
刑案的处理要关注社会效果,尊重生命,关怀人性,要更加务实。
聊城“假药案”未被认定为犯罪,正是这种情况。在山东省公安厅的指导下,聊城市、东昌府区两级公安机认为王清伟应王某光请求,转卖和帮助购买“卡博替尼”,并从中少量获利,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至于主任医师陈宗祥向患者推荐“卡博替尼”并列入医嘱的行为,则是未发现陈宗祥从中牟利,与药品销售人员不存在利益关联为由,认定为不构成犯罪。
与之类似的还有,重庆版“药神”案。
被告人李可在广州市以人民币400元/盒的价格从他人处购买可用于抗癌的“吉非替尼片”(即印度版“易瑞莎”)后,以500元/盒销售给在某医药公司工作的贺雄,贺雄又以1300元/盒的价格销售给他人。李可、贺雄二人分别非法获利人民币7000余元、56000余元。两人先后被抓获,经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上述“吉非替尼片”未经批准进口,应按假药论处。一审法院认定二人有罪,判处缓刑。二人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时对二人免于刑事处罚。
还需注意的是,聊城“假药案”中尚有一个细节,王清伟转卖的“卡博替尼”来自于段某真处。“山东公安”通报信息显示,“另据侦查,段某真自2017年11月以来,大量代购、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境外药品并从中牟利,将另案处理”。
可以看出的是,对于“假药”代购行为,是否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司法机关具有极大的弹性,主要关注的是患者有偿代购还是其他人员代购,再以量大量小予以区分,但是这种区分方法仍然未能具体考量销售行为的危害性同时伴随着销售行为的普惠性。
《药品管理法》以及《刑法》的修订,导致的案件持续不断,使得情理与法律的碰撞频繁的被摆在公众面前。目前来看,“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毕竟只是一种缓和的折中立场。特别是,此种规定的裁量权自由度过高,遇到有担当的司法者,或者会考量社会效果,顾全人性与生命。
且不论段某真以及其他类似案件的最终走向,这种问题的碰撞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缺乏危害后果的罪状条款,以及将具有医学疗效的仿真药、进口药一律认定为“假药”的处理方式,是不是过于机械,这种现象是不是需要解决。
有观点指出,不具有医学疗效的假药,应当予以打击,可以不考虑用药的危害后果;对于代购未经批准的进口药、境外药等具有疗效的药品,毕竟能够救助很多的癌症患者,需要法律具体考虑用药的后果。面对这种碰撞,法律该何去何从,应当纳入立法者的关注视野,避免现实的司法困境一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