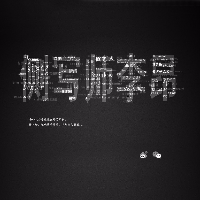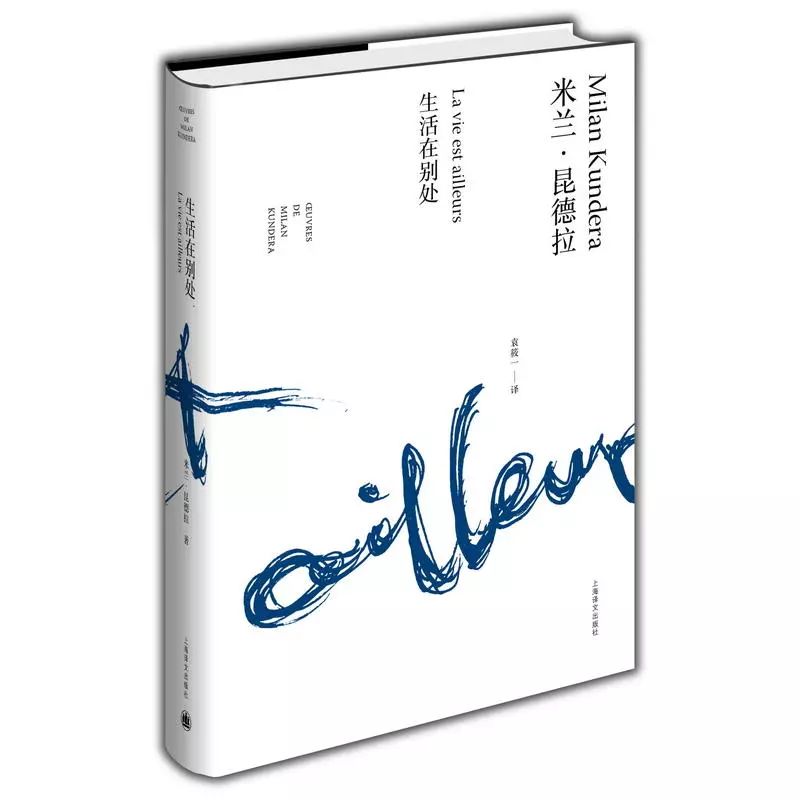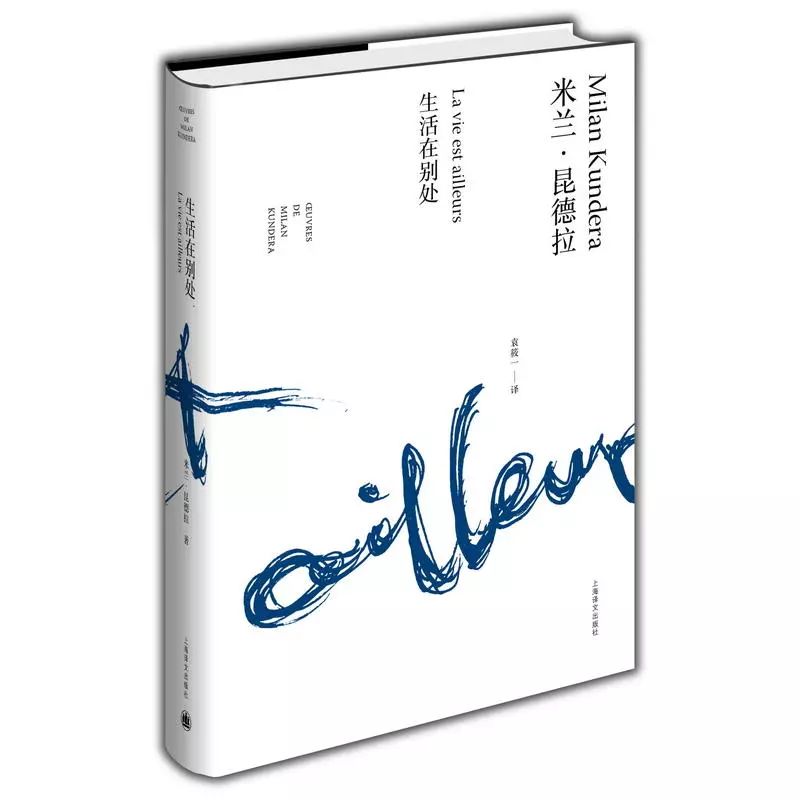
遇见是两个人的事,离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遇见是一个开始,离开却是为了遇见下一个离开。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怀上诗人的?
当他的母亲思考着这一向题时,似乎只有三种可能性值得认真考虑:不是某个晚上在公园的长凳上,就是某个下午在诗人父亲一个同事的房间里,或是某个清晨在布拉格附近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乡间。
诗人的父亲对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得出结论,怀上诗人是在他朋友的房间里,那一天特别倒霉。诗人的母亲不愿意去那里,为此他们吵了两架,后来又重归于好,当他们终于开始作爱时,隔壁房间有人大声地开门,诗人的母亲受了惊,他们停止了拥抱,慌忙仓促地结束了性交。他把怀上诗人归罪于这一瞬时的慌乱失措。
但是诗人的母亲却否认受孕可能是在借来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单身汉的邋遢地方,她厌恶那张乱糟糟的床和皱巴巴的睡衣裤),玛曼也否决了第二种选择:受孕发生在公园的长凳上,她当时很不情愿在那里做爱,一想到这样的长凳是妓女和行人常去的地方,她就感到恶心。因此她肯定怀孕只能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在绿色溪谷的背景上生动地衬出轮廓的一块巨石后面,布拉格的市民星期日常喜欢到这儿的溪谷郊游。
从多种理由看,这样的环境最适宜怀上诗人:在正午阳光的普照下,这儿是光明的白昼,而不是漆黑的夜晚;周围是广阔的自然,使人联想到翅膀和自由的飞翔;尽管离城郊的住宅不远,这儿的景致却有着浪漫的情调,到处都是裂罅、岩石和起伏不平的地面。当时这地点似乎生动地象征着她的经历。说到底,她对诗人父亲强烈的爱不正是对父母那种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浪漫的反抗吗?这块远离尘嚣、自由自在的风景区与她——一个富商的女儿——选择了身无分文的年轻工程师的巨大勇气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吗?
诗人的母亲一直陶醉在强烈的爱中,没有什么能改变这点,既使在那个美妙的下午,在那些圆石间的事仅仅几周后产生的失望也没有改变这点。她告诉情人每月烦扰她生活的那种不适没有按期出现。她兴奋万分地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他,可遇到的只是令人气愤的冷淡(现在我们回想起来,这种冷淡大半是表面上装出来的)。他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不重要的、纯粹暂时的和无关紧要的周期性生理失调而不予考虑。玛曼觉察到情人不愿分享她的欢乐后非常生气,直到医生正式宣布她已经怀孕了才跟他说话。当诗人父亲说他的一个好友是妇科医生,可以万无一失地消除她的烦恼时,玛曼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就是反抗的可悲结局!最初为了年轻的工程师而同父母对抗,后来又求助于父母来反对他。她的父母成功了;他们与工程师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他意识到别无出路,同意举行一次体面的婚礼。他欣然接受了一大笔嫁妆,这使他以后能建立起自己的建筑公司。他把他的全部财产塞进两只手提箱里,搬进他的新婚妻子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别墅。
尽管工程师迅速地妥协了,但诗人母亲仍然伤心地意识到她如此冲动地投进的这场冒险——它曾经象是美好得令人心醉——并没有变成她坚信有权期待的那种伟大的、彼此满意的爱情。她的父亲是布拉格两个生意兴隆的药房的老板,因此她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严格的平等交换的原则上。在她这方面,她把一切都投资到爱情中(她甚至愿意牺牲她的双亲以及他们那平静的生活);反过来,她也希望对方在共同的帐户中投资等量的感情。为了恢复平衡,她逐渐取回感情的储蓄,在婚礼后对丈夫摆出一副高傲严峻的面孔。
诗人母亲的姐姐不久前搬出了住宅(她结了婚,搬到了市中心的一个公寓),于是老两口继续住在楼下,他们的女儿和工程师则住在顶楼。楼上有三间屋子,其中两间很大,布置得完全和二十年前老药剂师修建别墅时一样。工程师就这样继承了一套家具齐全的房间。总之,对他来说这是令人满意的安排,因为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两只拼凑的手提箱,他完全没有任何财产。不过,他还是极力主张把这套房间作点小小的变动,但他的妻子根本不打算让他——这个乐意把她献到堕胎术者刀下的男人——粗暴地对待这个代表她父母精神、也代表二十年的良好习惯和安宁的世界。
在这种场合下,年轻的工程师也毫无反抗地妥协了,只是对一件事提出了小小的抗议:卧房里有一张小桌,桌上盖着一个沉重的灰色大理石圆盘,上面立着一个裸体男人的小雕像;雕像左手握着一把七弦琴,支在臀部上。右臂以一种动人的姿势挥出去,就象手指刚触拨了琴弦。右腿伸直,头部微微后倾,目光向着上方。这张脸非常美丽,头发卷曲如波,白色雪花石膏赋予他一种温柔的、女气的、也可以说是处女般的非凡神态;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滥用"非凡"这个词:根据刻在底座的铭文,这个手握七弦琴的雕像即是古希腊神阿波罗。
一看见这个雕像,诗人的母亲就不由得来气。这个神像经常被扭转过去,背部冲着房间,要不就成了工程师的帽架,要不那沉思的头就成了工程师搁鞋的地方。偶尔还有一只臭袜子套在小雕像上——这是对缪斯和她们的首领不可饶恕的亵渎。
诗人母亲异常愤怒地作出反应。这并不是仅仅由于缺乏幽默感,而是由于她相当准确地察觉到,丈夫把阿波罗套在袜子里是为了发出一个他出于礼貌不能直接表达的信息:以这种玩笑的方式,他要让她知道,他拒绝她的世界,他的屈服只是暂时的。
这具雪花石膏的雕像于是成了一个真正的古代神祗:一个不时介入人类事务,使人的一生困惑,设下阴谋,显示神迹的冥冥之神。年轻的女主人公把他视为同盟,她那充满渴望女性想象力把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瞳孔仿佛闪烁着生气,嘴唇颤动着声息。她爱上了这个为她而横遭凌辱的裸体青年。当她凝视着那张俊秀的脸时,她 产生了一个愿望,希望腹部里正在生长的孩子与丈夫这个风度翩翩的情敌相象。这个愿望如此强烈,以至她一面瞧着自己的腹部,一面想象着这个希腊青年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她祈求神运用他的力量改变过去,改变她怀上儿子的经历,就象伟大的提香曾经在一个拙劣画家毁坏的画布上画出了杰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