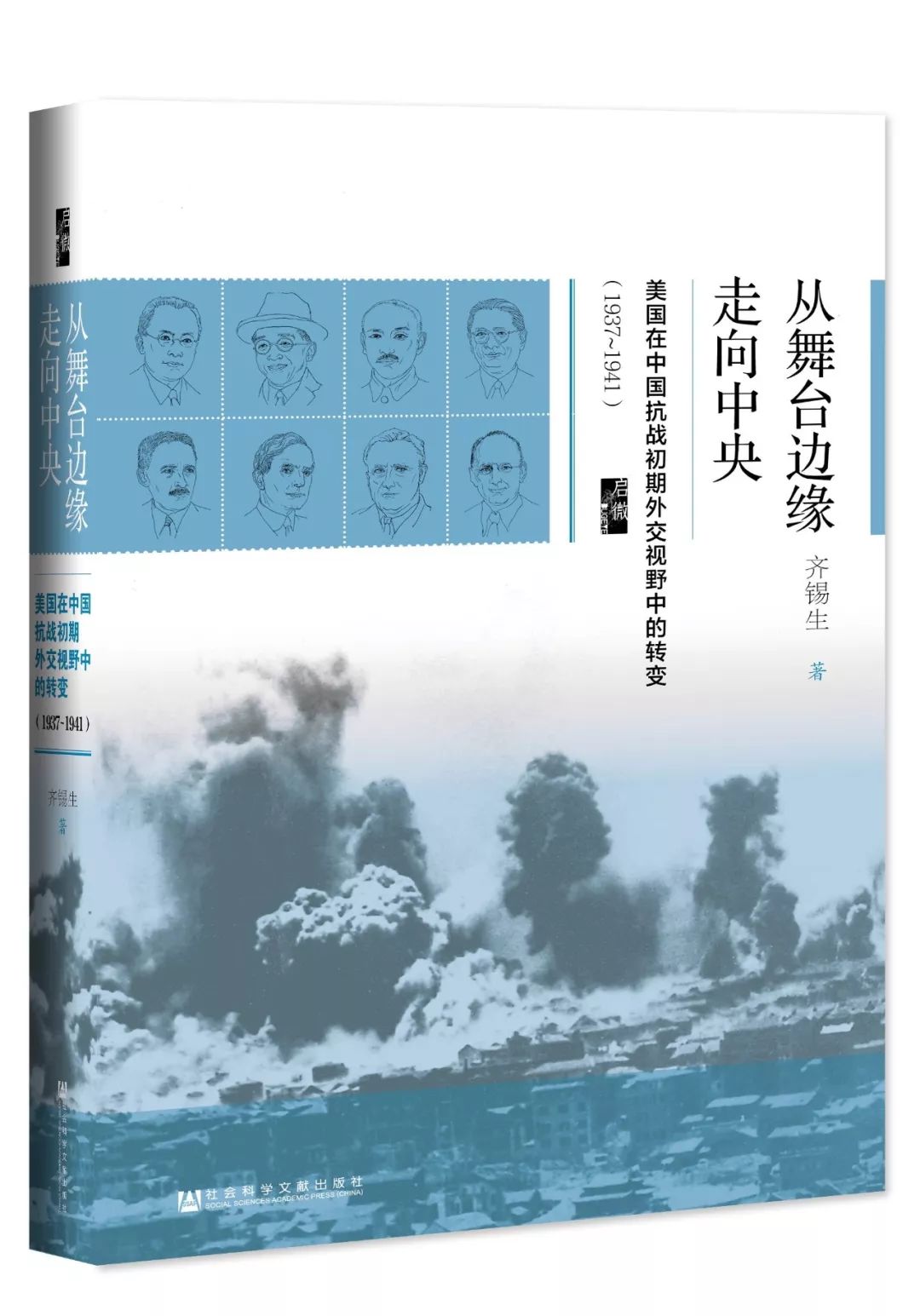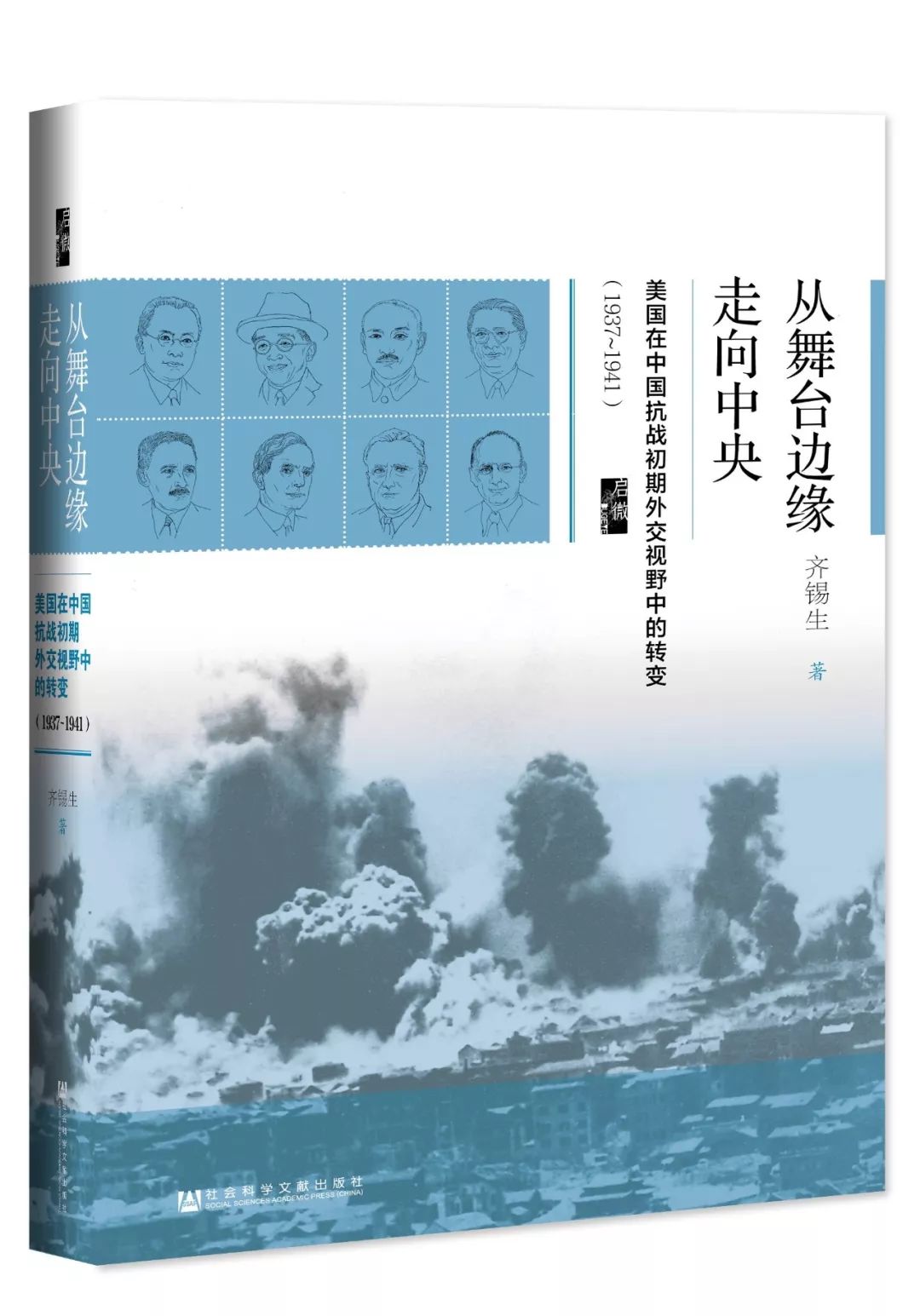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出版
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
期间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
中国政府对美外交的决策过程是什么?
由何人执行?
中国外交的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
美方的反应是什么?
中国政府在此期间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
何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
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战斗的盟友?
这些都是本书着力要探讨并希望解决的问题。
作者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018年9月,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以下简称“《舞台》”)一书的简体字版出版。作为长期研究中美关系史的权威学者,齐锡生的每一本著作都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是学界研究相关议题的必读之作。《舞台》一书聚焦于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可以视为《剑拔弩张的盟友》的姊妹篇。正如作者所言,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的中美关系很少引起学界关注,特别是在英文学术论著中,或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造成学术上一项“空白”。如何解读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中美关系,学界的既有认知是否正确?本书又在哪些方面有重要推进?这些都是研究抗战外交的学者希望了解的内容。
在进入正式的阅读之前,大致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及方法有助于掌握全书的内容精髓。作者在序言中直言,该书写作的目的是考察中国政府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比如中国外交的目的是什么?由何人执行?是如何谈判的?美方的反应如何?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得失?该书的写作方式是:“非常注意使用原始文件,除了参考堆积成山的官方档案之外,还尽量把中美两国关系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献文告或宣言”,同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异。在切入问题的角度上,《舞台》选择的是“关注中国的外交工作人员和他们外交工作的质量”,并努力避免把探讨的外交人物简单分成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1]在材料的使用和选择上,《舞台》采取的方法是档案史料和个人日记并重,在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较多使用了历史当事人的日记。
学界反思抗战后期的中美外交时,有一个大体结论,即“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实际上已失去美国的坚定支持,这不可不察”,“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了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2]从外交上而言,后期的离心离德是否已经在前期的交往模式中埋下种子?在更高层面思考抗战前期中美外交时,这也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齐锡生曾在另一本著作中,将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概括为“剑拔弩张”,国民党失去美国朝野同情与前期的交往模式有无关联?带着上述问题意识阅读《舞台》一书,有助于理解本书的整体观点。
一、中国边缘化美国还是美国边缘化中国?
检讨抗战初期的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在各自国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重新检视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最初因应是必要的,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情形下国民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启动国防预案,调派中央军赴华北。在最初的一周内,并未向外发出调停呼吁。需要指出的是,在事变之初,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启动军事预案,是因在此之前已经制定了对日作战计划。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方面的种种迹象符合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预设条件。1936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已经拟定《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并经蒋介石审阅。该计划对日本作战企图的判断与卢沟桥事变后的日军动向相吻合。《舞台》对事变之初国民政府的行动判断是准确的,与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是一致的。
在2000年之前,学界将蒋介石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政策总括为“和”与“战”的抉择,并在肯定蒋介石具有抗战决心的基础上,指出蒋在其内心仍有避免中日间发生大战的愿望。[3]这种判断现在看来是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在蒋介石“不挑战”但也“不怕战”心态之下,国民政府确实是在做两手准备,具体的对策就是:一方面致力于全面的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则呼吁列强的调停。
在最初的国民政府所准备的调停国家名单上,美、英、法、德、苏等国均在列。如果仔细梳理此时中国与英法两国关于调停卢沟桥事变的交涉过程,可以发现,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均将美国的参与视为解决中日冲突的关键。甚至在中国尚未发出呼吁调停之前,英法两国就已经主动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令驻美大使林赛(R. Lindsay)探询美方对于联合行动的态度,美方只同意“平行行动”而非联合行动。[4]法国则主动与英美两国沟通共同调停的可能性,并在事后告诉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美国的参与对于国联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卢沟桥事变后这段外交史告诉我们:美国此时被英法等国视为能够解决中日问题的决定力量。《舞台》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便是,为何中国不把美国视为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而是将其置于视野的边缘?转而去求一些次级重要的国家,如英法等。
在理解《舞台》所提出的问题之前,还需要了解当时的国际组织及其背后的运行机制。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此时能够依赖的调停机制有两个,一是国联,二是《九国公约》签字国。这两个国际组织是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实际维护者,从法理上能够调停中日之间的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上诉国联,并未能达到目的,通过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经验并未给英法带来希望,因此英法双方均不建议中国诉诸国联。1937年7月16日,国民政府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备忘录,其所倚重的正是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同日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美国希望中日不要发动战争,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5]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在评价赫尔的这个声明时称:“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知道是针对他们的,但声明的形式却使他们绝对找不到发怒的理由”。[6]美国的态度一方面可以解读为置身事外,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对日本不点名的批评。
国民政府此时并非不注重美国的力量,亦并非没有意识到其在远东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但关键在于美国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美国不但自身向中国表明此点,而且通过英法向中国表明了此点。在此种情形下,美国虽然是关键,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又能怎么样呢?虽然美方态度消极,但是国民政府还是最终做了一次努力,其结果就是1937年11月的布鲁塞尔会议。《舞台》强调:“中国政府致力于加强中美关系,把美国从外交视野的边缘移到中央位置,其最大动力来自中国态度的改变,认为美国具有最大潜能,能够给予中国最多的帮助去进行对日抗战。”[7]国内学界现有研究早已明确指出:“总体来看,国民政府在欧战爆发前的外交因应中,最为关注的是推动美国政策的变化和苏、英、法之间的合作进展。而美国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重点的思路,也在具体发展中逐渐清晰。”[8]
可否认为:美国虽处于核心位置,但只是一个旁观的巨人,因种种原因,其注意力不在中日冲突,中国所要做的,就是引起它的关注。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此时国民政府在战略上有无一个主要的争取国?目前来看尚难以确定。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国民政府此时所倚重的是集体仲裁。不论是诉诸国联还是通过《九国公约》签字国,都是此种思路。在外交上,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是促成事件的“国际化”,“让中日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使国际社会来参与中日冲突的解决,成了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9]
二、 如何评判胡适作为学者型外交官的外交使命与外交成绩?
研究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从方法论上而言,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那就是在国家战略框架之内,个人主观能动性能取得多大的突破?进而言之,驻美大使胡适是否有可能在美国的孤立政策与中立法内取得外交上的突破?对这个问题的恰当理解,可以为客观认识胡适的外交成绩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标杆。
(一)胡适使美的目标
▲ 胡适
《舞台》一书对胡适出任大使后的所作所为有非常全面、精彩的评论,作为一任备受争议的大使,《舞台》已经尽可能地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评价,并深入到了胡适本人的性格特质。《舞台》非常简洁地指出中国政府此时对美方朝野的认识,那就是“只想置身事外,保持美国的独立”[10],并认为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缺乏领导能力,不能提高使馆效率”。
作者指出:胡适在出任大使之前举办了大量的公共讲演,胡适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因为此时政府给予他的使命就是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王正廷不允许胡适插手正规外交活动;尽管演讲不能立即改变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至少可以在美国人民中建立对中国的好感;但一旦担任大使之后,胡适的工作重点就必须重新调整。[11]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之后,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目标是什么?胡适有无可能完成?这个问题与胡适出使美国的使命及其对自身的定位有密切关系。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将政府希望达成的对美外交目标分为五大问题:
1、欧战发生时,希望欧美在远东合作,防止英国届时对日妥协;“促请美国总统实行其隔离侵略者之政策,对日采行远距离的封锁”;“日本企图夺我主权、英法在华利益,望美勿置身事外,尤以维持上海公安局之地位及现状为要”。
2、修改美国中立法。“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日本未对华实行战时封锁前,仍望美国避免施用中立法”;“日本断绝中国交通时”,请美国对日本实施军火禁运。
3、最短期内争取到美国的现金或信用借款。
4、军用品售日问题,希望在飞机禁售的基础上,扩大到石油、钢铁的禁售。
5、随时报告美国朝野之主张及活动。[12]
外交部对胡适初任大使时所提出的期望能否作为评判胡适任内成绩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外交方针允许的范围内,胡适是否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这些都可以再讨论。但毫无疑问,《舞台》对于此点的多处论述颇能启发学界思考此问题。
接外交部指示电文后,胡适在致孔祥熙函电中强调“鄙意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对于胡适此电亦可从客观的角度加以理解,而非单纯从消极方面去判断胡适。胡适对于外交的理解与外交部所定目标是有关的,他将重点方向集中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以及朝野的对华同情上,即改变美国对华抗战的态度,促成英美在远东合作抗日,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至于借款、购械等具体事务,应该由专门人员负责,并不意味着大使馆不参与,也不意味着大使本身超然事外。胡适或许只希望做一个联络人或者监督者,当需要时他以大使的身份出面予以配合。对于此点,胡适甚至向孔祥熙举例予以说明:“光甫兄等来后,借款事空气顿肃清,即是最好例证。”[13]
(二)胡适对于中国抗战究竟做了何种贡献,有无可能量化?
《舞台》对胡适的抗战贡献进行了集中的阐述,而这是以往学界讨论较少的领域。在第二章第五节,作者总结了五个方面的成绩,认为胡适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对日和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适态度坚决,“胡适对和平活动的反应极为强烈,绝不妥协,甚至主动予以抨击。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时逾越一个驻外使节应有的权限,紧紧盯住国内政治领袖们的一举一动”。[14]胡适使美四年外交成绩如何评判,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当然,胡适本身以文人出任驻美大使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如何把美国民间的同情心,转换成其政府对中国的实质援助”,可能是评判胡适使美期间外交成就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舞台》明确指出,这是胡适使美需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在美国没有改变中立法之前,以大使一己之力,有无可能争取到美国的实质性援助?具体而言,胡适使美成绩如何,能否以有无争取到美国实质援助为判断标准?考虑抗战初期中国对外援武器的迫切需要,争取到实质性的物资援助当然是评判驻外大使成就的一个标准,但不应该以此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毕竟能否获得实质性援助,个人的外交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并非单方因素所能决定。
具体实质性援助的实现是建立在一系列努力基础之上的,是若干前期工作的最后结果。首先要获得对方的同情,其次要使对方认识到有必要提供援助,而这些工作往往比获得实质性援助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正如书中所言,“若想改变美国政府对借款、中立法和购买武器的立场,则必须改变美国人民的认知和争取他们的支持。而就这两项任务而言,胡适的资历又似乎让他成为最佳人选”。[15]《舞台》的这句话或许是对胡适自我外交定位的最好阐释。
胡适具有坚定的抗战立场,对蒋介石说服国内的主和派起到了关键作用。书中对胡适此点的评价可谓到位。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坚决反对对日谈和,这与国民政府内部很多处于要职的官员态度不同。《舞台》在论述蒋介石的坚持抗战决心时,特别提及胡适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作者对此时主和与主战的分析可谓独到而精准:“尽管蒋介石个人在和战问题上早已采取了明确而强硬的立场,其他负责任和有爱国心并且头脑清醒的领袖,依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去论证和战的利弊”。“‘和平’没有和‘卖国’画上等号,它只是让中国去和日本讨价还价,争取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停止军事冲突”,“鼓吹和平的人也不认为他们自己比主战派更不爱国”。作者指出,在蒋介石身边,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部长王宠惠都倾向和平,但二人绝非亲日派。事实上,一直到汪精卫逃离重庆之后,可以自由公开讨论“和平”的环境才发生了改变。“以实质而论,孔祥熙和王宠惠对于和平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汪精卫非常相似,然而他们对蒋介石的政治忠诚度比汪精卫要深厚得多”,“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日,他们二人绝对不会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但问题在于孔祥熙、王宠惠的主和使得蒋介石处于一种微妙的环境下,虽然他们二人对于和战问题的政治判断与蒋介石不同,而蒋无法撤除他们的公职,因为蒋找不到如此可以信赖的下属,也无法对他们严词训斥。胡适在影响国内和战的决策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胡适从美国发回国内要求重庆政府必须坚持抗战的电报,对蒋介石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正面影响,也使得蒋有理由警告孔祥熙、王宠惠,赶紧停止和平论调,否则中国可能会失去美国支持。“事实上,胡适不仅尽力阻挡中国不要去寻求和平路径,也同样尽力阻挡美国不要去充当调停人”,胡适对中国外交的贡献不是以其能力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而是利用他的大使地位促使中国坚持抗战。[16]果如书中所论,即使胡适没能争取来更多的美国贷款,没能帮助购买来美国军火,但相较于其对中国抗战决心的贡献,又怎么能不予以热情的赞扬呢?
(三)如何看待胡适外交上的短板,批评的声音剑指何处?
胡适使美期间,他对于美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政治环境里的各种限制和困境,总是表现得能够充分体谅,而又让自己举止有度。每当罗斯福或是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在口头上表达对中国的善意,而同时又为他们无法做出具体援助行动而表示遗憾时,胡适的响应永远是赶忙劝告重庆政府必须体会美国领袖们的困境与善意,而不要给后者添麻烦。面对来自重庆政府的敦促,胡适采取迂回手法逃避之。“照理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运用说服力去为国家达到目的。如果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胡适在美国的任务基本上并未达成”。[17]
已有研究也指出,胡适使美四年,“尽管奔波忙碌,但从纯粹外交角度看,他的成绩实在太平常”,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争取美援,帮助陈光甫完成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及第二次滇锡借款;二是为中立法案一事奔走,说服美国搁置“现购自运”;三是阻止美日妥协,在1941年春美日谈判中,坚决反对美日之间牺牲中国的妥协方案。上述三件外交成就不是胡适一人的功绩,但毕竟是在胡适大使任内完成的。[18]如果考虑到外交部在胡适就任之初所给的目标而言,成绩不算太差,毕竟在这一时期美国逐步加大了对日的制裁,并开始从物质上援助中国。
学界在表述抗战初期的中国政策时,一般用“苦撑待变”来形象化概括。《舞台》对“苦撑待变”来源及内涵的分析与学界现有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了新的看法。《舞台》认为胡适的苦撑待变口号不过是唱高调,内容空洞,他从来没有说明,在国际局势“变”了之后,中国究竟能够指望得到何种好处。同时指出胡适苦撑待变模式的最大缺点是:“既缺乏想象力,又完全使中国陷于被动”,“胡适主张的被动型,最终含义就是放弃外交”。《舞台》指出,胡适提出“苦撑待变”是在1937年12月,而蒋介石在同年10月底的日记中已经提出了关于“苦撑待变”的思路,也比胡适所言更为缜密,更为有逻辑。[19]
1942年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不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不敢与倭妥协,终主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舞台》认为,“以上一段评判和感叹,大概非常准确地表明了蒋介石对于胡适使美全部外交生涯的总结”。[20]
以蒋介石日记里的评价作为对胡适使美四年外交生涯的总结,是否会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但凡看过蒋介石日记的人大概都清楚,蒋在日记里惯于用词严厉,其言语之刻薄有时实在出乎想象。当然,日记作为一种私人记录,抒发个人心中的情绪,并以之作为对正规文献的补充,有其特别之处。从其日记里可以发现他心中对某人的好恶,而此种个人的观感往往是在官方文献里看不出的。书中也承认“他(蒋介石)对于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没有给胡适丝毫功劳,对于胡适和美国人的关系,以及他在美国的活动做了露骨的批判”。言语之间,对于胡适明显是抱有不平的。
已有研究认为,“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人士对胡适的外交成绩过分苛求是不很公道的。他们对美国期望太高了”,国民政府忘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是根据它自己的需要来制定的”,至于后期美国对华援助的突飞猛进,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可供讨论,即自卢沟桥事变后直到德意日三国结盟,美国总共援助中国7000余万美元,而在这以后的两年内,美国援华超过2亿美元,“足见,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取决于中国的需要,更不取决于中国驻美大使的才干;而是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美国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但不幸的是“当美国对华政策转机到来的时候,他(胡适)已从对美外交的中心被挤开了”。[21]
对于胡适在使美期间的外交成绩,《舞台》的评价既注重了胡适对于争取美国民心的基础性工作,也批评了胡适对于争取物质援助的惰性。正如书中所言,在均宣称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本书试图对于那些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因素能够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包括这些人的学识素养、品行个性”。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本书的叙述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三、关于抗战前期中国外交两个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舞台》对胡适的批评中,其中一点是胡适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存在过于理想的认识,这当然是有其根据的。然而批评者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胡适对美外交政策的态度?胡适是否坚定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一定无可置喙,中国无须干预自可得到理想结局?
(一)胡适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针对胡适在美外交活动,《舞台》曾从其个性出发予以解读,认为“胡适随和的个性和他对于美国政治的高度信赖,似乎是不谋而和”,即使在其还没有担任大使之前,就已经对美国政治做出了几个引人注目的结论,由于有了这些结论,在担任大使之后“坚信中国根本无法也无必要去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其原因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乃是由有远见的领袖们所制定,因此当然是目标鲜明,充满理性和一贯性”。[22]
在亨贝克文件中,此次谈话记录时间是1937年10月14日晚,胡适与亨贝克两人约谈了一个小时。此时胡适刚到美国两周,这是他与亨贝克的初次会谈。在会谈后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亨贝克高度评价胡适,称其“可能是当今中国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领袖”,并称赞其一向“远离政治”。报告称胡适“最近几个月以来坚定支持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与蒋介石等其他政府高层保持有密切联系”。在此次会谈中,胡适告诉亨贝克,他此次来美,既不是官方代表,也不是一个专门的游说者,他只是一个观察者和评论者。(亨贝克在报告中夹注解释:胡适分析眼光独到而敏锐,堪比李普曼。)在向亨贝克讲述中国形势时,胡适称:蒋介石已经尽力避免军事冲突,尤其是在上海地区,并相信日本近卫内阁亦是希望避免全面敌对的。但事情的发展远超双方的预料,尽管没有任何一方希望发展成敌对状态。谈到罗斯福总统的芝加哥演说时,胡适表示他本人既感到惊喜又备受鼓舞,表示总统的演说与国联的决议是平行的。胡适还表示,他本人充分认识到美国公众对和平的渴望以及避免战争的决心,为此,他本人不盼望美国政府比上周的立场走得更远,不希望美国卷入战争。[23]
《舞台》指出,胡适总结得出的美国政府引人注目的结论有三个:
1、美国领袖们在1937年7月已经有意识地制定出一套条理井然的远东外交政策,而且从此坚定不移地遵循该政策,既不犹疑也不矛盾;
2、美国该项政策的基本精神是谴责国际无政府状态,捍卫国际秩序,其目的远远不只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国民、投资和贸易,而且要捍卫国际关系更基本的价值和秩序;
3 、罗斯福终将会“隔离”国际侵略分子,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将会有效地抑制侵略行为并维持国际法和国际秩序。[24]
在亨贝克的报告中,胡适的结论总共有六点,其中第五点是:罗斯福总统芝加哥演说八个月来,美国的外交和海军政策正朝着隔离侵略者的方向逐步前进;第六点是:尽管从官方形式上美国政府对远东采取了无可指责的“中立政策”,但美国领导人正通过勇敢地谴责“孤立”来教育美国民众,以须捍卫国际法律和秩序来说服美国民众。[25]
在向亨贝克表达了上述对美国政策的认识后,胡适表示他无意要求亨贝克对上述观点进行证实或提出质疑(并强调亨贝克的官方身份也不允许他这么去做),而是让亨贝克知道他所理解的美国政府的政策。胡适紧接着向亨贝克提出了对美方的四条建议,并希望通过亨贝克转达美国政府。胡适认为,只有基于此种理解的背景,亨贝克才能同意向他本人并通过他本人向美国政府提出下列建议。
胡适所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希望美国能够采取实际行动而非消极等待,以便实现“防疫隔离演说”中的政策。胡适称,他认识到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理想政策的实现需要积极建设性的领导行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不幸事件的发生,正如“帕奈”号被击沉那样。他真挚希望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能够在远东地区排除困难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去停止可怕不公正的战争。胡适指出,很显然,通过采取有效的经济封锁以便坚定支持采取“隔离”侵略者的政策,可以防止侵略一方不遵守美国的和平呼吁,如果能做到此点,则美国所呼吁的和平实现机会很大,而且不会将自身卷入战争之中。胡适进一步表示,如果能让中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则此种积极争取和平的成功机会更大。为了得到明显效果,胡适建议美国应尽快采取行动,因为若中国不能再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则此种政策将大打折扣。[26]
胡适的第二个建议是美国必须马上干预中日战争,以防止中国崩溃。胡适称,“那种认为中国可以军事自救,日本将会被自身经济崩溃而击败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他指出,过去的11个月,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以极端的努力抵抗日本优越的机械化装备,这种极端努力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中国最终会因精疲力竭而倒下。“我坦陈,只有在美国政府领导下的国际干预下中国方能自救成功,这么说我不以为耻,因为1914年的法国即使做了44年的战争准备如果没有美国领导的国际参与,也无法自救。”[27]
第三个建议是,必须在广州、汉口沦陷前采取援助中国的行动,如果晚于这个时间,就可能来不及了。胡适告诉亨贝克,一旦广州武汉沦陷,则通过粤汉铁路的出海路线将被封锁,中国政府和军队将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胡适还表示,试想一下,现在正在江苏、安徽、浙江前线作战的大批部队将面临可怕的困难,中国的税入几乎全失,现在的物资运输路线失去出海口,即使是人力资源亦将大为减少。总而言之,“如果认为中国值得营救,那就必须在中国统一高效的中央政府倒下之前采取救援行动,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政府中国用了11年的时间”。[28]
第四个建议是,呼吁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去阻止战争,召集中日双方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通过第二次华盛顿会议或第二次布鲁塞尔会议解决中日冲突。[29]
在信函最后,胡适称,他向亨贝克所提四点建议事先并未得到中国政府授权,这些建议纯粹是一个致力于追求国际和平人士的个人要求,是一个毫无保留地深信美国政府政策人士的个人希望。胡适还表示,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信的内容,包括中国政府,他也不渴望一定得到亨贝克的回答,但如果亨贝克愿意会谈,可以随时电话联系,他本人将于7月13日启程赴英。[30]
胡适虽然在信函以及谈话过程中,对美国领袖们及其制定的方针政策表达了由衷的赞赏,并坚信可以达成目标,但其目的并非要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静默等待。其在对美表达了赞赏之后提出了迫切而明确的援助要求,并警告美方,不要等到中国已经倒下后再来援助中国,那样就来不及了。
(二)中国政府何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军事结盟方案?
《舞台》提及,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合作”这个概念的内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给予明晰界定,只是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次,“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军事联盟方案,因为它显然认为,仅是用西方列强的外交力量和声势(比如说,召开国际会议)就可以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舞台》认为,蒋介石一直在极力推动一个国际性的反日大同盟,“更不在意美国是否参加其事”。到了1940年底,中国才把建立一个对抗日本国际体系的设想变成具体的建议,并指出,在认知层面上,“胡适从来不赞同大联盟的想法”。[31]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学界发现,1939年2月11日海南岛沦陷之后,蒋介石已经提出了中法英军事结盟计划,计划还希望能让美、苏两国加入。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国民政府外交部草拟的中法英合作计划如下:
1、“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与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敌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
2、“参与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
3、“在军事方面,中国允尽量供给兵力、人力及物力,其他各国允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其详细计划及实施办法由参与各国各派军事全权代表一人商议决定,分别执行”;
4 “在经济方面参与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其详细计划及实施办法由参与各国各派经济全权代表一人商议决定,分别执行”。
外交部在电文中强调“此事系蒋委员长发动,目下欧局急转之下,此项计划值此时或有若干可能,惟上开原则已经蒋委员长核准”,要求顾维钧迅速密商法国政府,并于3月24日发出该电。[32]蒋在日记中自记,其对英法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必使远东问题加入欧局之内”。[33]就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国政府在1939年初已经向英、法、美、苏等提出了一个可以讨论的军事结盟方案,此方案为以后的真正结盟提供了一个蓝本。
四、 宋子文使美与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
▲ 宋子文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做战争准备的同时,力图为全面开战赢得尽可能多的准备时间。为达到此目的,国民政府一再向以英法主导的国联求助,并一再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九国公约》签字国求助,希望能够利用现有的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现有研究亦认为,基于英美实力的消长变化及对华政策的差异,抗战初期的中国外交侧重点有一个调整,即“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围绕远东危机的若干次交涉活动也表明,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不肯也不能有所作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变化,日益重视对美外交,并在1938年中逐步完成了外交重点的转变”。[34]
学界注意到中国外交在抗战初期有一个转变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在外交方针上确立了一个主要的求援国,观察视角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从外交行动上看,此时国民政府在外交形式上是将英美法苏并列的,只要能有助于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都曾极力予以争取。如果从援助效果而言,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援助是最多的,那么能否认为苏联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呢?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的对华援助也远大于英美法,能把德国认为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宋子文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出使美国,在时间上正好与中美关系的加速升温高度重合。
《舞台》第四章集中阐述了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原因,并将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时间段确定为1939至1940年间。作者提出,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原因,一是国际环境剧烈变化,包括日本战略改变对中国造成了影响,中国日趋严重的军火危机,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二是中国国内情势加速恶化,包括财政困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挫折;三是中国对美国观感的改变。第四章论述的中国改变对美政策,并不是说由原来的疏离美国变为亲近美国,而是说中国将美国视为外交求援的重中之重,在此意义上,这里所说的改变对美政策事实上是加强对美求援。可以这样认为,虽然国民政府一直在强调争取美援的极端重要性,但现任大使胡适被蒋介石认为“执行不力”,而且拒绝改变工作思路和态度,不得已,蒋介石只能另辟蹊径,再派宋子文去执行。自此后,中美外交开启了“个人外交”模式。在整个第七章,作者以相当的笔墨论述了蒋、宋个人外交的特色及取得的不俗成果,并单辟一节对个人外交作了评估。
(一)关于宋子文使美的目的及评价
学界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在战时外交体制内,宋子文从事特殊外交使命,而并无正式官方身份,原因之一在于“抗战之初在重要职位调动问题上,蒋介石并无一言定夺的权力,仍必须遵守相应体制的制约”,宋子文出使美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全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直至出任外交部部长。[35]《舞台》指出,当蒋介石在1940年4月初开始争取让宋子文同意赴美时,只是想让他解决中国内部的财政困境,但是不久,就改为解决最为重要的向美国贷款问题。到了6月决定派遣之时,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个助手去替他积极有效地处理中美关系,于是宋子文被任命为特使。“赋予宋子文的任务是去谈判一些借款,购买一些武器,然后希望美国政府在越南和缅甸问题上可以采取坚定态度”,完成这些任务,宋子文就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宋子文有自己的想法,一是宋主动希望延长滞留美国的时间,以便做出更大成就;二是对自己政治出路的盘算。宋子文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回国就必须与蒋介石和孔祥熙纠缠,如果留在美国又受胡适的掣肘而无法发挥自己的能量”。[36]
在美期间,宋子文与美国官方的互动关系创造了一个新局面,这一是因为宋子文“在中国政坛上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二是因为“宋子文抵达美国后,美国的政治环境也和1937—1940年大不相同”。《舞台》也指出,这两点是胡适所不能比的。[37]在宋子文主导下,1940—1941年的中美关系在四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分别是经济援助、军火购买、越南和缅甸通道的重新开放,以及促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结盟。
在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时,《舞台》对胡适与宋子文的性格进行了比较,认为二人完全不同。宋子文会“毫不迟疑地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那里榨取出最大的政治利益”,“无论何时在和联邦官员打交道时,他都会毫不迟疑地跑到罗斯福那里告御状”。宋子文“毫无疑问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舞台》更为明确地指出,宋子文的最大目标“是帮助中国在当前逆势下获得更多的武器和贷款”,为达到此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对美国采取了间谍手段,而胡适则“极为珍视自己的形象和羽毛”。比较而言,“尽管宋子文的某些手段可能带来较高风险,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所能发挥的功能远远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38]
到了1941年,美国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求援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舞台》所表述的核心概念: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经过胡适的前期工作和宋子文的特别努力,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初具雏形,这种特殊关系事实上是以美国对华的物资援助为主要特征的。在美国成为中国外交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宋子文的出使恰逢其时。虽然强调了宋子文个人外交风格的重要作用,但《舞台》仍将国际局势的变化作为论述的基本背景,并非置客观环境于不顾。
在《舞台》展开第七章“1941年:美国迈向中国外交舞台中央”时,将“内外”情势作为该章的开篇论述,客观上认为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加强向美求援的力度。此时国民政府完成了对美外交的另一个形式上的转变:开辟了私人外交的通道,先是颜惠庆,接着是宋子文。《舞台》认为,此时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在宋子文的参与下,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并具体举出宋子文与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交涉,指出:“中国人不再唯唯谨谨地依照美国人颁定的行为准则办事”,宋与摩根索的交往,“大概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外交官面向美国领袖,双目逼视而没有做出丝毫退缩动作”的案例,为中美官员互动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39]
(二)中美外交的转变,是中美同时加速,还是只有中方在加速?
中美关系的转变,前期之慢与后期之快,多大程度上是外交官个人作用所致?《舞台》对此有详细的论证。先是宋子文访美,建立起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私人联系渠道,然后邀请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通过居里明确了个人外交渠道的建立。紧接着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随后,美国军方开始派团访华,先是空军代表团访华,随即组建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然后是陆军代表团访华,宋美龄在个人外交渠道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些活动都是在宋子文访美之后发生的事情,并且在进入1941年之后有一个加速的趋势。中美之间这一连串的外交互动与宋子文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宋子文如此努力,为何在学界仍存在大面积的批评声音,这是一个经常引起关注的现象。
即使是在肯定宋子文外交成就的论著中,亦不讳言宋的缺点。一般而言,宋子文在使美期间的外交作风颇受争议,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独断专行,独揽外交事务;二是不按通讯程序展开工作,甚至隐瞒消息或删改指示;三是重视个人外交;四是好用公共外交,有时沦于操纵。其雷厉风行、独断专权的作风使他集毁誉于一身,但如果细看宋子文在外交上的作为,“对中国而言,不但有相当的突破性建树,而且为外交界也注入了不少活力与新作风”。[40]
个人外交某种程度上是领袖外交或领袖外交的延伸。[41]如果离开双方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支持,这种个人外交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简而言之,个人外交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直接、高效,直接由最高领导掌控,绕过政府的外交行政部门。《舞台》对中美个人外交的功效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居里访华建立起了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个人联系渠道,罗斯福亦有意通过个人渠道直接解决问题。“居里的访华,肯定加强了他们的信念,认为个人外交的确远比通过政府部门正常运作的方式来的既快捷又奏效”。蒋介石和宋子文之所以热衷推行个人外交,不是为了故意颠覆美国正常行政运作程序,而是因为中美双方都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是增进两国关系的一种极为可取的方法,并断言“中美双方领袖都一直希望依赖个人外交途径去处理事务”。从美方而言,因为人尽皆知,罗斯福“对于传统外交部门工作人员缺乏信任,也不尊敬他们的专业能力”。《舞台》的论证说明,美国罗斯福总统不但倾向于建立个人渠道,而且其程度甚至远超蒋介石本人。“‘个人外交’绝不是中方‘不识大体’或是蓄意颠覆美国行政体系的计谋,而是中美元首的共同意愿”。[42]美方对中国所建立的这条私人外交渠道存在很多的批评,对于宋子文完全抛开美国国务院的做法,即使是居里亦希望宋子文能够有所收敛。居里在1941年11月底告诉蒋介石,“美国有些领袖已经对中国政府只依赖宋子文这个渠道向美国政府各部会传递外交文件的做法感到无法接受,认为这种做法有违国际惯例”。指责宋子文的声音主要来自美国国务院,但这种指责“不代表美方对中方整体的评价,只是宣泄它自己被罗斯福冷落的不平,不敢向罗斯福抗议,只能拿中国出气而已”。[43]《舞台》反驳认为,这完全是双重标准,事实上,最善于运用个人外交的领袖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个人渠道所决定的事情,美国政府官员“不但不敢批评,还要心存愧疚,责备自己没有及时‘体察上意’”,而罕有人责备丘吉尔。[44]在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主动权是在美国手中还是在中国手中,这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美国成为中国外交舞台的中心,是美国主动走向中心,还是中国拉美国进入中心?目前而言,似乎美方的主动性并不比中方的主动性差。思考清楚上述问题对于理解宋子文外交的成效也是有帮助的。事实上,由于实力的不对称,美国始终掌控着主动权,美国方面只要对华释放一分善意,就将换来国民政府至少二分的回应。宋子文使美外交成就的获得,固然有其个人的积极主动性,而且我们要充分肯定这种个人主动性的作用,但对美国方面希望改善中国关系的努力亦应重视。如果没有美国方面的回应和改变,抗战前期中美关系不会出现一种加速的态势。
现有的材料表明,美国方面对于日本意图控制中国的侵略行径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国务院、海军部会不时地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华给予援助。在“帕奈号”事件之后,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Harry E. Yanell)就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盟友,挫败日本图谋的唯一办法是援助中国进行抵抗,只是由于中国的抵抗,日军才没有进军加利福尼亚。到了1938年年中,摩根索致信罗斯福:建议美国必须从1931年以来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而不能再犯英法两国短视的错误;在美国还能用和平手段制止侵略的时候就赶紧去做。研究者指出,在抗战初期“美国常常在中国抗战遇到严重情况的危急时刻宣布新的措施”。[45]
关于个人能动性与世界大势的作用,《舞台》有一段精彩的说明,“尽管胡适正确地预测世界大局的发展对中国有利,但是美国民意的转变并不能视为胡适的功劳,因为世界大势远比胡适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此种判断逻辑不知是否可以挪用到宋子文身上?抗战后期美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成为舞台中央主角,若并非宋子文的功劳,那么是否因为世界大势使然?
结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迅即成为盟友。学界早已存在的一个基本疑问是:战时中美两国的结盟为什么不仅未能促成双方的深入了解和接近,反而最终酿成了两国的长期对立?这个问题并非《舞台》一书论述的重点所在,但通过书中抽丝剥茧的分析以及宏观和微观的论述,能够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路。从根本上而言,促进中美之间接近的真实因素是日本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打破了美国政治家们关注的远东势力均衡。[46]中国对美外交在此背景下得以成功转型,建立起了特殊意义上的中美关系。《舞台》对抗战前期中美关系的深入剖析为理解这种转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更加注重国民政府外交的方法和人选因素。
在抗战初期,中国处在美国外交的边缘,还是美国处在中国外交的边缘?从实际政策效果而言,可以认为中美双方互相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是对等的。从历史上看,美国自一战后就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远东太平洋区域,美国拥有实际的地区发言权,华盛顿会议就是这种实力的体现。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是中国政府力争的对象,非常希望能借重美国的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但不论是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还是在美国视野中中国问题的重要程度,都不足以使其将中国视为外交的重心所在。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态势,美国开始改变态度。《舞台》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些鲜活的细节。
在抗战初期的中美外交关系中,驻美大使胡适与蒋介石特使宋子文两相比较,如果从个人外交模式去考察,其成效显然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或者说成绩的大小,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整个抗战大局及二战发展形势而决定,是一个智者见智的问题。“形势比人强”,是一句俗语。驻美大使所透视的中美关系只是一个侧面,其重要性在整个中外关系中究竟几何,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将其置于整个抗战前期外交的大背景中,其所占分量或许又要打个折扣。
如果将胡适、宋子文在美外交活动比喻成基础性研究与实用对策性研究,究竟孰优孰劣,大概还是要取决于不同的评判角度。正如《舞台》所言“胡适所关心的是‘大’问题,因此他的报告着重分析这些大问题”,“宋子文更关心当前的实质收成”。[47]对于重功用的蒋介石而言,眼前的实际功效的获得失去了美国长久的信任,造成了盟友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美国最终放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
如何运用日记的个人记录来丰富档案中的历史,本书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尽管日记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在解读历史当事人个人心态上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作用。档案文件表面文字之下,谁又能确定执行者是真的赞成所发电文的原意?对于日记而言,当事人对事件的判断及有关人物的臧否,与档案所揭示的事件的经纬及自然发展过程,仍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学术研究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毕其功于一役的研究也只能是理想的境界。《舞台》提出“历史学要求不断改善和推陈出新,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是尊重史料,讲求方法。两者缺一不可”。[48]该书通过对抗战前期中美关系的解读,将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我们在理解此时期的中美关系时,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告和电文,还理解到其背后外交当事者的个人情怀及喜怒哀乐。其优点所在,亦是其弱点所藏,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难以求全。
参 考 文 献
[1]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03页。
[2]王建朗:《抗战研究的方法与视野》,《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第15页。
[3]王建朗:《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4]“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Hornbeck)” (July 14, 19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 Vol 3, The Far East,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pp 160-161
[5]《赫尔声明》(1937年7月16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7卷上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2页。
[6]约瑟夫·C 格鲁著,蒋相泽译:《使日十年——1932至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5页。
[7]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493页。
[8]彭敦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页。
[9]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68页。
[10]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5页。
[11] 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65页。
[12]《外交部致胡适电》(1938年10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
[13]《胡适致孔祥熙电》(1938年10月),《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3页。
[14]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105页。
[15]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56页。
[16]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106、108、118页。
[17]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143、150页。
[18]耿云志:《胡适与抗战》,《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57—58页。
[19]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151—152页。
[20]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473页。
[21]耿云志:《胡适与抗战》,《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59页。
[22]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135页。《舞台》此论断来自1937年10月15日胡适与亨贝克(S. K. Hornbeck)的谈话记录以及1938年7月胡适致亨贝克的信。
[23]“Hornbeck note of conversation with Hu Shih”(October 15, 1937),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Hornbeck Papers, Box80
[24]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135页。
[25]“Hu Shih to Hornbeck”(June 9, 1938),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Hornbeck Papers, Box80
[26]“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 (June 9, 1938),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Hornbeck Papers,Box80
[27]“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 (June 9, 1938),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Hornbeck Papers,Box80
[28]“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 (June 9, 1938),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Hornbeck Papers,Box80
[29]“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 (June 9, 1938),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Hornbeck Papers,Box80
[30]“Hu Shih Letter to Hornbeck”, (June 9, 1938),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Hornbeck Papers,Box80
[31]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104、300—301页。
[32]《外交部致顾维钧电》(1939年3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手稿与珍本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Koo/0021/027/0011。
[3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3月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34]王建朗:《战时外交:从苦撑待变到大国擘画》,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43页。
[35]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史学月刊》2017年第11期,第81页。
[36]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217、221—222页。
[37]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231页。
[38]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227、231页。
[39]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329—330页。
[40]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61页。
[41]参见杨闯主编《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168页;赵可金:《外交学原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3页。
[42]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337、
[43]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503页。339、503页。
[44]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375页。外交学界论述“首脑外交”时,一般会以丘吉尔为嚆矢。见杨闯主编《外交学》,第162—168页;赵可金:《外交学原理》,第252—253页。
[45]关于抗战初期美方的政策,见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46]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参见章百家《不对称的同盟: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第16页。
[47]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231页。
[48]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第498页。
本文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