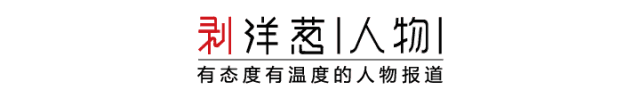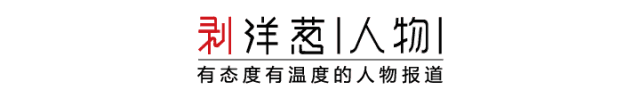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提倡的“非锁国”的爱国精神,则是近代以来新思潮之集大成,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与渊源。
1919年5月7日,被拘捕的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学生释放返校。
►时光荏苒,一转眼五四运动已经100年。100年前,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之一,但五四的爱国精神却是一种带有启蒙意义的救亡运动。正是启蒙的救亡,或者说为了救亡的启蒙,使五四爱国精神突破、超越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复杂、丰富的思想内容,成为“新青年”应有的爱国精神。
《新青年》的创刊号刊登了陈独秀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其中一点是希望青年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因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立所不能,亦且势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爱国却不盲目排外,爱国却不闭关自守,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深沉的理性思考,这些新青年精神面相难能可贵。
18世纪德国思想家康德写下了著名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五四一代当然深受这种“世界主义”影响,但他们积极主张世界主义,却并不完全是受这种外来“世界主义”纯观念的影响,而主要是出自对自身所处现实、民族危亡的深刻思考。
如何救国?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认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因此改造“国民性”,便成为爱国、救亡的迫切任务。这样,救亡与启蒙,便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起来。
救亡是青年的责任,但只有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青年才担得起真正能救亡的重任。这种新思想新观念,就是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新青年”应“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这种观点与康德的思想如出一辙,提出要有勇气打破外在的枷锁,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世界。但是,“固有之智能”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知识体系、结构和理论框架。对世界的认识、看法,正是由这种认知系统决定的,不同的认知系统,对世界的看法大不一致。
所以,在社会转型时仅有勇气还是不够的,要完成这种转型,同时需要认知体系的变更,应该用新的认知系统取代旧系统,因此,他们才提出“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
只有用科学精神、态度审视世界,才能感觉、发现旧制度的不合理,要建立新制度。“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社会的发展进步有赖于“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日的中国若“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事实上,梁启超对如何处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宋教仁对“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早就有所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提倡的“非锁国”的爱国精神,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戊戌维新之后形成的新思潮之集大成,也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与渊源。
而今百年过去,尽管形势变了,但这股新青年精神气质依然没有过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它会沉淀为深厚的精神遗产,并迸发出推动社会前行的能量。
文/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五四运动历史报道集锦
1919年5月4日的那个下午,在之后的反复叙述中衍生出了种种迥异版本,耐人寻味。仅在次日的各大报刊报道中,关于许多细节就有不同程度的出入与情感表达,这些或一手或二手的现场报道对于进入与理解“五四”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等报纸对“五四”事件后的持续跟进也为后来者勾勒了一幅影影绰绰的时代全景图。百年来,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幻,“五四”始终是一个思想源泉,一个精神地标,被一代一代的人不断挖掘和阐述,回首这一个世纪的“五四”论述,我们也得以管窥时代精神的延续与变迁。
1919年5月5日
北京《京报》
《学生界之大风潮》
闻昨日午后三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高等农业、高等工业、法政专门等五大学校,更有私立之中国大学等聚集三千余人,排队赴总统府、天安门并至东交巷英美法意驻京使馆,随处欲举代表发言表示国民对于外交之真正意思,并要求各使维持公理主持公道。
惟行至东交民巷口,公使馆方面以无中国政府执照不许通行,乃举代表数名,赴各使馆接洽,其他众学生等乃转而赴东城赵家楼曹汝霖宅内,警察等阻拦不住,拥入寻觅曹汝霖,曹已避去。当时学生举动非常文明,而因警察之干涉手段惹起学生之反抗,无意中将宅内电灯碰破,遂至宅内起火。
火光中双方撕打,伤及在曹宅闲住章仲和公使,而且伤势甚重,并闻曹之侄公子亦受伤,于是警厅派警察及保安队三百余人赶到,弹压始行解散,而警察乃捕去学生七人(并非为首者)。
天津《益世报》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
《益世报》1919年5月5日关于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的漫画。
各学生至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已将大门紧闭,并有警察把守。各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簷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下,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钱、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当时有一学生,从玻璃窗钻入,将大门开放,各生遂一拥而入。其临街为花园所有花草均被蹂躏践踏,又捣毁器具。园内有本国及日本人数名,学生有识之者,指日:“其中有章宗祥!”欲围而殴之,有一生以砖头击章首,血流被面。
各日人卫拥章出后门,匿一小洋货店内。各生遂趋内宅觅曹汝霖,一日人出曰:“我即曹汝霖,汝辈欲制死曹,可先制死我。”各生恐酿成交涉,遂置曹不究,但捣毁各房屋器具。此时火已起矣。传闻起火原因有二:一说因电灯被砸,电火溢出;一说系曹家人自放。
天津《大公报》
《北京学界之大举动》
欧议中之青岛问题至近日形势大变,我国朝野均奋起力争,而北京学界尤为愤激,乃于昨日星期休假,国立大学及各专门学校学生举行游街大会,以为国民对于外交表示誓争到底。
午后一时许,各校学生结队数千人在天安门集,各执白旗大书: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宁死,取消二十一条等语,此外尤多激烈之词。步军统领李长泰闻信亲莅天安门,约各校代表说话,代表说明志在争回青岛,绝无扰乱秩序之事发生。
李统领亦鉴学生爱国热忱,允即谒见总统,将学界意见转达。各校学生遂列队游行至东交民巷,持函谒见各国公使,请主张公道。乃游行回校,沿途秩序井然,观者塞道,无不为之感动。
北京《顺天时报》
(日本汉文报纸)
其言论亦可管窥当时的社会状况。
《北京学生大骚动》
是时章氏自公府宴会归,身穿礼服,正在曹宅,不防该生等陡然闯入。章氏急难逃避,遂被群众所殴,受伤甚重。群众因搜索曹氏,未得其中暴烈份子遂举火焚房。当时火焰冲空,人生鼎沸,曹氏邻舍家家闭门,恐惧不堪。
当该生等在中华门齐集时,警察厅仅传知各区巡警注意所往,不料其有此种暴烈之举动也,比见群众放火烧房并将章氏殴伤,一面保护曹氏眷属迁出,一面召集消防队救火,一面电知大总统请示办法。旋经大总统传紧急命令,提署暨警察厅逮捕肇事首魁。
群众见军警捕人始皆逃散,当时被捕者约有二十余名。闻章宗祥氏迨群众去,始入同仁医院调治。……曹汝霖闻此惊耗,不敢遽归私宅,遂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暂避该事,结果如何俟访续登。
1919年5月6日
上海《民国日报》
“北京专电”
京中各校学生,因山东问题失败,昨晚集众游行街市,为有秩序之国民示威运动,共二千余人。
北京大学学生最多,至东交民巷被阻,经过曹汝霖宅,欲入内诘问,为警察以武力干涉,众皆愤怒,当入宅打破电灯,曹宅焚毁,曹偕眷逃避六国饭店。章宗祥此次来京,住曹汝霖宅,学生入内时,未及走避,被殴受伤甚重,现送入医院。各校学生归途,被军警拘捕二十余人。
今日各校全体停课。段祺瑞主张置各学生重典,钱阁昨晚开紧急会议,多主解散北京大学,傅增湘力争未允,今日已递呈辞。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愿以一人抵罪……
1919年5月7日
上海《时报》
《上海报界电北京政府》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北京学生行动虽激,然实出于爱国热诚。顷闻有主解散学校、处学生死刑之说,风声所播,舆情愤激。须知压抑欲重,反动愈烈。际此国家存亡所关,全恃民气激昂,为政府后盾。请勿漠视舆论,致激巨变。望立开释被捕学生,以慰人心。上海日报公会。鱼(6日)。
1919年5月8日
北京《晨报》
《被捕学生全体释放》
1919年5月7日,被拘捕的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学生释放返校。
四日被捕之三十二名学生自被拘以来,舆论愤激,佥谓非立请政府释放不可。是晚,即首由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三人具呈保释,并由三君面谒总统,陈述先行释放之必要。而当局未许。翌日,复由十三校校长及山东国会议员联名呈保,亦未之许。六日,熊希龄、王家襄、范源濂、张一尘、高而谦等五人及天津十校长亦联名呈请保释。
上海《申报》
《书业决定“五九”停业》
望平街书业商会于7日开临时会议,佥以后日为5月9日,实二十一条签定之纪念,议决各同业于是日停业一天。一方对于欧洲和会表示吾国民之决心,一方对于北京学生表示敬意。
附:书业商团同志会致该业商会书,略谓:窃维吾业为文化传布机关,尤与教育界有密切关系。日来欧洲和会,拟将青岛问题归中日自行解决,北京大学及诸专门大学学生,群起击贼以示威,此实国家之荣光,不可忽视者也。沪上学生团体既开国耻纪念会,闻风而响应矣。则吾业更不可不有所表示,以为社会之观感,亦以尽国民之责任。兹拟于本月9日,即民国4年吾国承认日本无理要求之国耻纪念日,凡吾同业均停业一天,于门首各悬“国耻纪念”白旗一面,而兴亡之责,亦可聊表寸心。即请俯准,转知同业,一体照行。并望函知上海南北商会,请其转告各业致仿照办理,则国家幸甚,本会各业幸甚。
《新申报》1919年5月5日发行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号外。
1919年5月9日
四川成都《国民公报》
“要电汇志”
北京全体学生愤曹汝霖等之卖国,群至曹贼,请曹质问,曹知事不妙,逃;章宗祥被殴重伤,群生将曹宅焚毁,被捕数十。
1919年5月11日
上海《每周评论》
《山东问题: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
后来大家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巡警、宪兵、游缉队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几位学生不管危险,从天窗上跳进去;后来把门敲开,大家一齐进去,打东西,找曹汝霖,一面打一面哭,巡警也有哭了的。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苏佩秋,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都没有打,放了出去,只捉曹汝霖不到。
这天晌午,曹和陆、章三人都在总统府宴会,有人劝曹不要回去,曹说怕些什么,所以就同着章宗祥回家,就碰到这桩事,大家把章宗祥捉到,打了个晕倒血流,头盖上露骨。先是一进曹家就有火起——据说是曹宅家人放的--到这时候,火势已大,不能再停,一齐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就带队赶到。
曹看打人的已去,才从老妈子的房里出去,大喝吴氏疏忽,还说:“你快快把这些不知道曹总长利害的混账学生全给我捉去!”吴有点迟疑,他又说:“有我哩!”吴才下令捕散去后剩下的学生,捕到三十三人。然而曹也不再停,坐着吴氏的汽车,带着武装,揣着秘密文件一箱,直往东交民巷。交民巷的巡捕因为他车上有武装,行的又太快,把车夫、汽车捉了去,他一个人只得躲到六国饭店去。
陆徵祥(左二)、章宗祥(左三)、曹汝霖(右一)。
1919年5月15日
北京《晨报》
《昨日之教育界消息》
蔡元培辞职出京,学界方面一再挽留,尚无结果。昨日总统特发指令,劝留其文如下:
呈悉。该校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至高等专门各校长系向教育部具呈辞职,当局闻讯,已切嘱教育部从速批留,惟因教育总长傅沅叔离京,部中无人主持,致未能即时批出。至傅氏踪迹,据其家中人言,四五日不见,正在寻找,惟昨日有人见自汤山回宅。昨日批留蔡校长,今亦由傅氏亲笔署名云。
自慰留蔡氏指令发表后,各校职教员联合会去电通知蔡氏,并一面派代表赴杭面邀蔡氏回京。至于蔡氏联袂辞职之各校长,亦由该会派代表数人到各校长家中劝其回任,学生联合会亦拟代表偕同赴杭云。
1919年6月5日
北京《晨报》
《愈闹愈大之学界风潮》
自前日学生重行讲演被军队拘捕多人,而后形势愈益重大。据昨日所得各方面消息,则学生之讲演仍在继续进行,而军警之拘捕亦依然不放松,以目下情形观之,学界风潮犹在继长增高,尚无收束之端倪也……
昨日各校学生仍四出讲演,被捕者较前此尤多,大约有七八百人之谱,综合前后已达千人以上,法科各讲堂遂有人满之患,乃更拓理科大讲堂为补充之地,因之而理科大学昨日亦成为拘留所矣。又闻昨前两日教员学生均有受伤者,其中二人昨已送往首善医院医治云。
1919年6月17日
北京《晨报》
《北京学生对于陈独秀被捕之表示》
警察总监钧鉴:敬启者,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
特举出二要点如下:(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
(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想见忌于一般守旧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基此二种理由,学生等特陈请贵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实为德使。
本文原载于5月4日《新京报》B04-B05版。整理:杨司奇 徐学勤;编辑:杨司奇 榕小崧;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洋葱话题
▼
你如何理解“五四精神”?
点击“阅读原文”
查看“五四100周年·新青年”特别策划
推荐阅读
蒋方舟:30岁,我才刚上场
邢立达:与恐龙对话的“网红”科学家
“北斗女神”徐颖:我不是网红
“诗词大会”夺冠后,外卖小哥婉拒“百万年薪”成“雷老师”
与癌症谣言“死磕”,高学历的人也不懂癌症
守护莫高窟的年轻人
腾格里沙漠里的80后:把沙漠种成“花海”
为无声者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