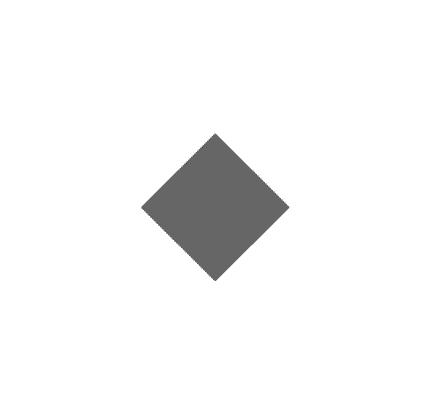简介
近几年,美国自由主义滑向了一种对种族身份、性别身份和性身份的道德恐慌,这使得自由主义的信条被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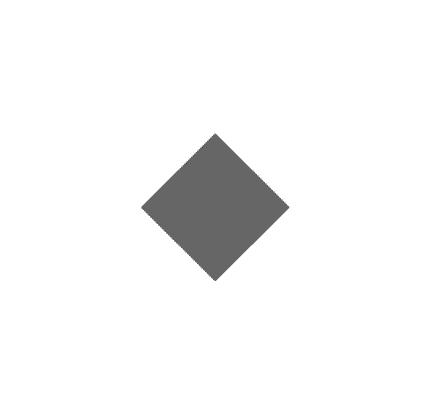
作者:Mark Lilla(马克·里拉)
邵依琳译、马华灵校
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多元的国家,这是老生常谈了。这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美妙之事。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来自那些难以接纳不同族群和信仰的国家的访客,讶异于我们的成功。自然,这并不完美,但美国确实比当今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都要好得多。美国的故事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成功故事。
然而,这种多元性(diversity)究竟该如何塑造政治呢?对将近一代人来说,标准的自由派答案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差异,并“赞美”我们的差异。对于道德教育来说,这是一条极好的准则。但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把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却是灾难性的。近几年,美国自由主义滑向了一种对种族身份、性别(gender)身份和性(sexual)身份的道德恐慌,这使得自由主义的信条被扭曲,并且使之无法成为一股可以支配的统一力量。
△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
最近的大选及其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产生了许多教训,其中一个教训是我们必须终结身份自由主义的时代(the age of identity liberalism)。当希拉里·克林顿谈论国际事务中的美国利益及其与我们所理解的民主的关系时,她处于最佳状态,并且最振奋人心。但在国内事务上,她却在竞选活动中丧失了那种大视野,并滑向了浮夸的多元言辞。在每个竞选站,她都明确向非洲裔、拉美裔、LGBT和女性选民高声疾呼。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如果你要提美国的群体,就最好提及所有。否则,被遗漏的群体会有所察觉,产生被排斥感。数据显示,白人工薪阶层和有着虔诚宗教信念的人正是这样的群体。整整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和百分之八十的白人福音派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身份认同的道德力量当然有许多正面影响。平权法案重塑并改善了共同的生活。“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给每个有良知的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好莱坞努力使同性恋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正常化,而这有助于同性恋在美国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正常化。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但我们的学校和媒体对多元的执念培养出了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者。他们对除自己归属的群体外的状况一无所知,对接触各行各业的美国人的任务也不甚关心。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他们有个人认同之前,就被鼓励去谈论他们的个人认同。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多元性话语已经穷尽了政治话语,以至于他们竟然对阶级、战争、经济和共同善这些持久的问题感到无话可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高中历史课程时代错置地把当今的认同政治投射回过去,从而曲解了曾经塑造美国的主要力量和个人。(比如,女权运动的成就是真实和重要的,但如果你不首先理解国父们建立这个基于权利保障的政府体系的成就,你就无法理解女权运动的成就。)
△女权运动
当年轻人进入大学时,他们被学生社团、老师和全职处理“多元议题”并拔高其重要性的行政人员鼓励继续关注自身。福克斯新闻和其他保守派媒体极力嘲讽围绕着这些议题所产生的“校园疯狂”,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嘲讽是正确的。而这只能让民粹主义煽动者无意中占了便宜,他们想要从从未踏足校园者的视角出发来使学习丧失正当性。当面向普通选民发表演说的时候,如何向他们解释赋予大学生选择指定性别代词来使用的权利的所谓道德紧迫性?如何又能不和这些选民一起,嘲笑写下“国王陛下”的密歇根大学恶作剧者之事?
这种多元校园的意识在这些年来已经逐渐渗入了自由派媒体,这是可以觉察的。美国报纸和广播所倡导的针对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是一个非凡的社会成就,它甚至已经改变,并且确实改变了右翼媒体的面貌,记者梅根·凯利(Megyn Kelly)和劳拉·英格勒姆(Laura Ingraham)的成名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似乎也鼓励了这种假想(尤其是在更年轻的记者和编辑中间),即只要把精力集中于身份问题上,他们就已经完成他们的工作了。
△平权运动
最近我在法国学术休假期间做了一个小实验:在整整一年中,我只读欧洲出版物,不读美国出版物。我的想法是,尝试从欧洲读者的视角来看世界。但更有意义的是,我回到美国后才意识到近年来身份的透镜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新闻报道。例如,美国新闻里“第一个做某事的什么人”之类的最马虎的报道不知讲了多少遍。这种对身份剧情的痴迷甚至影响了对国外的报道,而十分苦恼的是,这类报道原本就匮乏。比如说,无论阅读埃及变性人命运的故事有多有趣,它对教育美国人理解决定埃及未来且间接决定我们自身的政治和宗教浪潮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主要的欧洲媒体会考虑采用这样的视角。
但是,正如我们不久前所见的那样,在选举政治的层面上,身份自由主义遭遇了最惊人的失败。健康期间的国家政治关注共性,而非差异。而且,国家政治的主导问题是,谁能够把关于我们共同命运的美国想象描绘得最好。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罗纳德·里根的构想,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巧妙。比尔·克林顿也是如此,他借鉴了里根。他把民主党带离了身份意识那一边,并且集中精力于能够造福每个人的国内项目(如全国性的健康保险),还界定了1989年之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因此,克林顿才能够在两个任期中为民主党阵营中的不同群体作出重大贡献。相反地,身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只动之以情,而非晓之以理。这就是为什么身份政治不能赢得大选,却会输掉大选的原因。
媒体对愤怒的白人男性产生的近乎人类学的新兴趣,既揭露了我们自由主义的处境,又展现了这个被多次诽谤且此前被忽略了的人物。自由派对最近总统大选的一种省力解释是,特朗普先生的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把经济劣势转化为种族仇视——白人对抗的议题(the “whitelash” thesis)。这是一种省力的解释,因为它允许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并且让自由派忽略了那些选民所说的首要关切。这种解释同时助长了一种幻想:从长远看,共和党右翼注定会在人口上消亡,这意味着自由派只需静候这个国家落入自己手中。但是,比例高得惊人的拉美裔在大选中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这应当提醒我们,族群在美国越是持久,在政治上就越是多元。
△唐纳德·特朗普
最后,白人对抗的议题之所以是一种省力的解释,是因为它赦免了自由派的以下罪责: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身对多元的执念,如何使得具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乡村白人认为,他们是一个身份受到威胁抑或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反对美国多元化的现状(毕竟他们倾向于住在美国同质化的地区),而是反对无处不在的浮夸的身份政治言辞,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政治正确”。自由派应该铭记,美国政治中的第一次身份政治运动是至今依然存在的三K党。那些玩弄身份政治游戏的人,应该做好失败的准备。
我们需要一种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post-identity liberalism),而且它应吸取前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pre-identity liberalism)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这种自由主义将吸引作为美国人的美国人,并突出那些会影响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议题,从而扩大其基础。它将针对作为公民国家的国家而言说,而公民们应该团结起来,而且必须互帮互助。至于那些范围较窄、在象征的意义上代价高昂、并且可能会赶跑潜在盟友的议题,特别是涉及性取向和宗教的议题,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会低调、谨慎且适度地加以处理。(不妨改写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言论:美国已经厌倦于听到自由派该死的厕所问题了。)
信奉这种自由主义的教师们,应当将注意力重新放到他们在民主国家中所承担的主要政治责任上来:形成认识到自己的政府体制和我们历史中的主要力量及事件的忠诚公民。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还应强调,民主不仅仅关乎权利,还需要公民承担责任,如知情和投票的责任等;后身份政治的自由派媒体,应就被忽略的那部分国土及那部分国土上的重要事务(特别是在宗教上),开展自我教育。媒体应当认真承担起教育美国人的责任,尤其要从历史的维度,介绍塑造国际政治的主要力量 。
△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1月6日在国会演讲
数年前,我受邀参加佛罗里达的一个工会大会,在一个分会场就罗斯福1941年所发表的关于四个自由的著名演讲做发言。那个会场坐满了来自地方分会的代表——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拉丁裔。我们通过唱国歌开场,然后坐下聆听罗斯福演讲的录音。我环望人群,看见那些不同的面孔,我被他们对共同分享的东西所表现出的那种专注所打动。罗斯福呼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认为这四种自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当他呼吁这四种自由的时候,他那激动人心的声音提醒了我,什么才是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根本 。
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