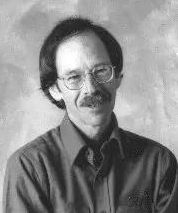哲学与人工智能的交汇访休伯特·德雷福斯和斯图亚特·德雷福斯
原载《哲学动态》2013年第11期

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 1929- ),国际知名的现象学家,是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研究的权威。他的影响不限于哲学界,他蜚声世界的贡献是从现象学立场出发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的哲学预设的批判。德雷福斯教授发表过学术论文160多篇,主编了现象学方面的论文5部,出版著作8部、哲学类音像制品3部,接受各国媒体采访60余次。其代表性著作有:《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理性批判》 《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诠释学》 《心灵高于机器》 《在世》 《行动中的思想:论因特网》等。
△采访者:成素梅、姚艳勤
☆受访者:休伯特·德雷福斯、斯图亚特·德雷福斯
成素梅:大家好!我们是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成素梅和姚艳勤……
休伯特:Hey, guys! 我们是休伯特和斯图亚特…
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以下简称休伯特)教授从1960到1968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哲学教学工作。196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哲学与文学教学工作。他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被誉为海德格尔工作的最精准和最完整的解释者。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与弟弟斯图亚特·德雷福斯(Stuart Dreyfus,美国计算机专家和神经科学家,以下简称斯图亚特)合作,从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批判传统的人工智能研究,之后,进一步把研究视域扩展到对一般人性问题的思考。
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纪念休伯特德雷福斯哲学研究的两本论文集:《海德格尔、真实性与现代性:纪念德雷福斯论文集1》和《海德格尔、应对与认知科学:纪念德雷福斯论文集2》。罗蒂在第一卷的导言中认为,休伯特的工作填平了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鸿沟。
2005年,休伯特荣获美国哲学学会的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颁发的巴威斯奖(Barwise Prize)。休伯特的工作生动地证明,哲学家也能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发挥作用。现在,80多岁的休伯特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在第一线。为了进一步理解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他们围绕技能获得模型所折射出的哲学思想,我们邀请休伯特进行一次学术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他的弟弟斯图亚特也在一些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休伯特曾于2009年6月23日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在他访问期间,我们曾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过交流。本访谈是近期先通过电子邮件然后进行电脑视频来完成的。
一、关于现象学的问题
问:休伯特教授,您好,我们首先想了解的是,您从现象学出发对人工智能提出一些看法,是否起到了作用?
休伯特:我对哲学家们能够充当科学技术的批判者这一角色很感兴趣。因此,我作为一名哲学家,曾受政府基金管理部门(比如国防部)的邀请做他们的投资顾问。他们问我,向符号化的人工智能提供资助,是否有价值。我说,“肯定没有价值”。于是,他们停止了对这个领域的资助,然后,人工智能就进入所谓的“寒冬”期。这意味着,没有人再从事这项工作。我不能说,这是我造成的,我只能说,我的看法被当局采纳了,我赢了。
问:您认为您的哲学观点主要来源于海德格尔,那么,在您看来,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休伯特:海德格尔是一流的哲学家,他看到,应对技能是建立在所有的可理解性和理解之基础上的。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其他哲学家,特别是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但重要的是,海德格尔说的话,听起来像是斯图亚特的技能模型,也就是说,当你成为一名专家时,你完全融入到情境当中,并且,以不再有“你”的方式,全身心地投人其中。当一名运动员在比赛中处于最佳状态时,他完全被比赛所吸引。这就是海德格尔的伟大思想,因为他试图拒斥400年来一直深受欢迎的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也就是在哲学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重要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观点。笛卡尔说,人是独立思考的个体;海德格尔说,不,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沉浸在世界之中。人是活动和工具的整个语境的一部分。海德格尔摧毁了笛卡尔的权威。现在,仍然有一些笛卡尔的信徒,但是,也有一些人知道,当我们是专家和表现出最佳状态时,我们并不是独立的人。我们被完全吸引到整个情境当中。我们的生存方式基本上是被卷入的(to be involved),海德格尔就是揭示了这一点的第一位哲学家。
斯图亚特·德雷福斯
斯图亚特:我来补充一些内容。学习开车的一位初学者把自己看成是操作一台机器的某个零部件。这被称之为是分离的立场。当一个人成为一名专家级的司机时,他感受到自己是要到达某个地方。在这一点上,他被卷入了世界。
问:那么,在您们看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在现象学界和哲学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休伯特:在所有的哲学发展中,海德格尔摆脱了笛卡尔的观点。他不相信,人是用心灵表征世界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是独立的智者,心灵拥有所有的图像本身,这些图像属于外部世界。这只是斯图亚特描述的“初学者”的方式。海德格尔采用“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这个概念,意指完全被世界所吸引。那就是“专家”。
斯图亚特:就我们的七个阶段的技能获得模型(model of skill acquisition),即:
(1)初学者阶段;
(2)高级初学者阶段;
(3)胜任阶段;
(4)精通阶段;
(5)专长阶段;
(6)驾驭阶段;
(7)实践智慧阶段而言,
前三个阶段是分离的。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有一个大的突变。在精通阶段,人们有了对情境的卷入感,而不是与所处的情境分离开来做决定。这种感觉只能来自经验。然而,在第五阶段,需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都是被卷入世界的结果。人们完全沉浸在技能的世界中。
休伯特:当你们摆脱了笛卡尔的思想时,你们也就摆脱了大约1650年以来完全相信笛卡尔的所有哲学家,比如,休谟、斯宾诺莎和康德等西方哲学史上的所有这些大人物。如果你们理解海德格尔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在心中拥有世界的图像,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还导致了对世界的那些表征是否符合实在的疑问。只有当我们达到理论反思的水平时,或者说,当我们开始获得一项技能时,这才会发生。
问:您们在阐述技能获得模型时,经常会引用梅洛-庞蒂的观点,那么,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之间有什么异同呢?
休伯特: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俩人的观点基本相同:当我处于最佳状态时,我完全被世界所吸引。但是,除了差不多三个句子之外,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谈到“人有身体”这样的事实。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我们在这里不研究这一问题。”此外,他也没有谈到知觉,知觉是我们看事物的主要方式。他认为,我们有身体,但重要的是,我们抓住了身体;我们有知觉,但重要的是,我们抓住了知觉。但这恰好不是他想要谈论的话题。海德格尔承袭了哲学,但仍然有未完成的工作:那就是,说明如何把我们的身体纳入到哲学的讨论当中,以及我们如何感知所融入的世界。梅洛-庞蒂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接受了这一任务。
问:在您们所阐述的哲学观点中,熟练应对似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这样吗?
休伯特:是的,熟练应对是一切的基础。熟练应对就是我们处于最佳状态。这是成为大师所必需的。对于处理问题来说,熟练应对很流行。
二、现象学与人工智能
给大家普及一下,百度百科上说: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先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问:1964年,您应兰德公司的邀请,评价艾伦·纽厄尔(Alan 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工作,他们开创了认知模拟(cognitive simulation)领域。您能告诉我们,兰德公司为什么会邀请您这位哲学家来评价似乎与哲学不相关的认知模拟领域内的工作呢?
休伯特: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把现象学和人工智能联系起来,那是一段令人着迷的插曲。分析哲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接受了笛卡尔看问题的分离方式,并把一切都看成是理性的、遵守规则的,等等。可我争辩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不可能获得智能。于是,他们就设法整我,把我赶出了麻省理工学院,理由是我借麻省理工学院的名望,提出了这些疯狂的观点。有趣的是,我是对的。现在,我赢得了老一代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尊敬,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他们运用规则不可能获得智能。我花了许多时间讨论常识和框架问题。不管怎么说,以这种方式,人工智能是无望的。分离的遵守规则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我们的行动和感知的基本方式。熟练的专家是不遵守规则的。
斯图亚特:我1955年到兰德公司工作。我卷人了思考如何用数学模型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的问题。我卷入的这个领域称为运筹学。1958年,赫伯特·西蒙在《运筹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西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也是兰德公司的顾问。直到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才知道他在做什么。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数学建模不能帮助人们做出决策。未来,运用人工智能能够比人做出更好的决策。因此,他在本质上是说,我和兰德公司研究运筹学的每个人都是误人歧途。就这样,我了解到,兰德公司卷入了人工智能的研究。西蒙的文章给出了人工智能在未来10年内将会实现的四个预言,其中的一个预言是,计算机能战胜国际象棋冠军。我就把兰德公司当时所做的研究和西蒙的预言告诉了我的哥哥休伯特。休伯特研究了西蒙等人的方法,他所感兴趣的哲学使他相信,如果以他们的方式来做的话,人工智能将会失败。
休伯特:我们应该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计算机如何能够战胜象棋大师。
斯图亚特:正如你们可能知道的那样,大约在西蒙提出10年内计算机能战胜国际象棋冠军这一预言的40年之后,运用模拟人的思维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世界锦标赛的质量。做到这一点,是用计算机算出了未来比赛中所有的可能步骤。因此,西蒙的预言不仅很不成熟,而且,他基于他处理人工智能问题的方式有权做出这一预言,他的这种信念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
休伯特:我们需要为人工智能新的研究方式起一个名称,这种新方式不是认知模拟——不是推理,不是遵守规则,而且,现在我认为,它是我不想用的那个词。当人们说符号化的人工智能时,那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类误解的另一个名称。当运用规则的人工智能在逐渐衰退时,我的一个学生,具有讽刺意味地把它称之为“好的过时的人工智能”(简称GOFAI)。我告诉你们,因为在我写GOFAI错在哪里的文章时,它是与认知模拟具有的错误一样的主题,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这只是笛卡尔式的支配技能模型的较低层次的规则。
问:您运用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批判传统的以符号表征为基础的人工智能,这可以看成是对现象学的一种应用研究吗?
休伯特:是的,重要的是,在哲学中,“现象学”这个名字有两种不同的用法。朴素的现象学仍然是笛卡尔式的,那就是,它仍然相信,心灵是独立存在的,心灵通过图像、表征与世界相符合,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会说,我们恰好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确实处于熟练的最佳状态时,我们是沉醉在世界之中。这种现象学并不能被称为“朴素的现象学”,而是被称为“存在主义的现象学”。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两类现象学是完全对立的。胡塞尔在一本他称之为《笛卡尔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的书中解答了朴素的现象学的问题。朴素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相差甚远。
问:您在1972年出版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一书中是运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对认知模拟和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假设、心理学假设、认识论假设和本体论假设进行了一一反驳。最后您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风险,不是超智能机器的降临,而是低智能人的出现。这种观点是否隐含了一种悖论呢? 一方面,超智能机器的产生需要设计者有更高智慧,另一方面,智能机器的使用,又会降低人的智能。比如说,与过去凭经验诊断的医生相比,总是借助于各种机器检测结果进行诊断的医生,其凭经验诊断的医术水平就会降低,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休伯特:那些认为技术将会排除技能的人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如果你有给某个病人做检査的心电图仪、核磁共振仪等所有的高科技仪器,难道你就对医生的医术没有要求了吗?心电图仪和核磁共振仪未必使医生的医术下降。也许他们将会得到看懂心电图、X光片等图像的技能。因此,高技术器械带来了一个不同的领域。
问:1949年10月27日在曼彻斯特大学举行的“心灵与计算机”的学术会议上,波兰尼向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标题是“心灵能够用机器来表征吗?”,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哥德尔和塔斯基的观点,阐述了人的直觉与判断的运用不可能通过任何一种机械论来表征的观点,并且,他还与图林、纽曼等人讨论了这个问题。您的观点似乎与波兰尼的观点很类似,您对波兰尼的观点有何评价?
休伯特:波兰尼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他的《个人知识》和《意会的维度》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两本书。他是一位不断钻研哲学的化学家,他向会议提交的文章很重要,他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心灵不能用机器来表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而且,他的意思也并不是说,当你在全神贯注地做某事时——他以盲人的拐杖为例——你的心灵好像不是分离出来看看这根木头的属性,然后,为它提供一种解释。事情不是这么发生的。你已经与这根拐杖融为一体,你在感觉着拐杖末端的世界。对于这一点来说,波兰尼是对的。但在一个有趣的方面,他是错误的。我曾遇到过波兰尼,我们还就他的《个人知识》一书中的一段进行过讨论。他在这一段描述了现象学,然后指出:“但是,我们当然是遵守规则的”。接着,他举一个例子,当你在骑自行车时,你为了保持垂直,必须向着摔倒的方向扭转车轮。你扭转车轮角度的大小,随着你的车速的变化而变化。就此而言,这就是一个规则。而我认为,这恰好是错误的。
斯图亚特:在人工智能之后,兴起了称之为神经网络和强化学习的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说,存在无意识的规则(unconscious rules),而是讨论大脑工作的方式,结论是,即使你不去学习规则,你也能学会骑自行车。你只是通过大量的实践掌握了骑自行车的窍门。神经得到了协调,这样,你就不会摔倒。因此,我只是想说,实际上重要的是,当你转而反对过时的人工智能时,你要意识到,你通过学习规则不可能获得技能,但是,你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技能。
问:您认为意会知识能够转化为明言知识吗?
休伯特:意会知识能够转化为明言知识,但不会捕获到技能。你能够发现意会知识的大致规则,并使它成为明言知识,但将失去技能和直觉。你充其量能达到高级初学者的层次,也许只是初学者的层次。
问:据说,您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一书被翻译成20种语言,巳经成为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甚至明斯基(Minsky)、麦卡锡(McCarthy)和维诺格拉德(Winograd)等人工智能专家已经在践行您的观点,人工智能专家会经常与您讨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研究吗?
休伯特:明斯基和麦卡锡是最重要的两位人工智能的研究者。维诺格拉德以反对人工智能而著名。他通过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发生了转变。因此,我们不能把维诺格拉德与明斯基和麦卡锡相提并论。明斯基和麦卡锡都错了。他们继续研究人工智能,不理睬任何人。只有维诺格拉德与我讨论问题。维诺格拉德巳经把我的观点付诸实践。其实,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已经失败了,没有必要讨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和伯克利有很大的公开辩论。每年都有大约300名学生集合起来争论过时的人工智能。但现在,我们知道,当你在应对时和处于最佳状态时,心灵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是初学者或当你反思你在做什么时,你才会意识到心灵。像明斯基和麦卡锡这样的人恰好没有看到这一点。
三、技能获得模型
问:您在运用现象学的观点思考人工智能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您与您的弟弟一起提出了技能获得模型;您们是如何想到要提出这样一种模型呢?您们认为这个模型的重要价值何在?
斯图亚特:就技能模型而言,我们提出这个模型与思考如何提高飞行员的应急反应技能联系在一起。我们要考虑如何最好地教飞行员进行应急反应。这致使我们提出了七阶段的技能获得模型。我们看到了前三个阶段是什么,因为我们关心对飞行员的实际训练。他们可能需要从运用人们提供的规则开始。但是,必须很小心,当你训练飞行员时,他们明白,这并不是在他们成为专业人员后最终处理问题的方式。因此,飞行员为了能够学得更好,他们需要规则,以便能够得到经验。但是,在教学中,必须告诉他们,当他们最终掌握了驾驶技能之后,就不会再根据现在所学的这些应用规则来驾驶。许多教育的失误在于,开始时不会告诉学生这些事情。当用了越来越多的规则使得技能的履行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时,应该告诉学生,当他们成为真正的专业技术人员之后,技能将容易得多。我认为,对于教育来说,技能获得模型的最大意义在于,有必要让学生准备采取困难的阶段三和比较容易的阶段四之间的步骤。这就是对哲学家的观点的困难理解与更自然地获得像哲学家那样的思考能力之间的区别。
问:在这个模型中,最有新意的地方是,当学习者达到了语境敏感阶段时,他对问题的处理就变成了直觉式的熟练应对,也就是说,他只是根据掌握的技能随机应变地处理眼前的问题。您们认为,这种经过训练获得的直觉与人天生的本能之间有什么异同呢?
斯图亚特:“本能”是在出生时大脑中预编程序的某种东西。本能包括当你的手遇到火时会自动缩回。对于鸟类来说,如何筑巢。在我的理解中,“直觉”完全是建立在通过经验来学习的基础之上的。许多人误以为,直觉不一定需要通过经验来拥有。在某种程度上,你可能不可思议地知道,你在自己没有经验的情境中或类似的情境中去做什么。
问:您们在阐述技能获得模型时,多次使用了“无理性”和“无意识”这样的术语,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斯图亚特:对我们来说,“无理性”意味着,没有使用技能模型的前三个阶段。我们发明了这个术语,但我们使用它时,与无从区分是非(amoral)这个词的用法一样。这意味着,我们不用推理或进行分离就能搞清楚去做什么。非理性意指运用了错误的推理。无理性意指不用进行推理。无意识意指,我们不能说明,你为什么这样做事。除了专家的直觉的熟练应对是无意识的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联想思维。你向一个人提供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或你想到的一种观念。无意识包括,除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脑神经元的突触引起事情的发生之外,这个人不能说明什么。
问:您们在阐述熟练应对时,多次强调情感卷人的重要性,并认为,学习者嵌人语境的程度越深,对语境的敏感程度就越高,这种现象也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情况。但是,您在《心灵高于机器》一书中,并没有对科学研究的情况做出更多的阐述,大部分阐述还是立足于日常的技能活动,比如,开车、下棋等。那么,您能更具体地阐明一下,我们如何用这个模型来说明科学家的认知技能的获得情况?
斯图亚特:如果人们没有熟练应对问题的能力,就不能做科学研究。一般情况下,这个能力不可能像在许多活动少那样从反复试验中学到。相反,它是通过观察和模仿有技能的科学家的学徒关系学到的。当然,如果人们不知道关于科学的所有事实,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因此,科学研究是两种情况的结合:人们必须拥有在我们的技能获得模型的前三个阶段中所获得的事实性知识,也泰须具备这个模型的后两个阶段的熟练应对能力。
问:库恩认为,当科学理论处于常规时期时,科学家只是运用现有的范式解决问题,而不对范式本身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只有到了科学革命时期,才对范式提出批判。您们的熟练应对是否类似于库恩的常规理论时期?您们如何评价库恩的常规科学时期?
斯图亚特:就科学探索而言,我们的模型只应用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牵涉到创造性的问题。我们没有研究科学探索的特殊技能,但我猜想,关于常规科学,我与库恩有一点分歧。他把科学探索中采取的步骤解释成是受类似于过去记住的情境的感觉引导的。他确实意识到,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们似乎不知道如何提问或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哪方面类似?”我认为,认知神经科学的当前研究说明,人们不需要提问或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替代的观点被称为执行器—评价器时序差分强化学习。
问:根据这个技能获得模型,学习者从新手到专家的提升,只有在经过从语境无关阶段进人到语境敏感阶段之后,才有可能。如何来理解这个过程呢?
斯图亚特:我当前的说明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专长是通过强化学习各种不同的情况,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而产生的。成功的行动造成了对大脑中导致这种行动的神经元的突触的强化。
问:专长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那么,专家的创造性应对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专家为什么能做出情境化的反应并且表现出创造性?
斯图亚特: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成功地说明创造性。休伯特在他合作出版的《披露新世界:企业家精神、民主行动和团结的培养》一书中,触及到这个主题。我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论及这个主题。
四、关于当代哲学的一些看法
问:您们在2011年出版了《万物闪耀》(All Things Shining) 一书,在出版之前,还刊载介绍这本书的相关信息。这本新著进一步发展了您关于熟练应对的观点吗?
休伯特:确实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就是研究我所说的“实践智慧”这一最髙境界的社会技能和人们如何获得这项技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各种无情的“流畅自如”的选择,可是,我们的西方文化没有向我们提供明确的选择方式,我们的书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这种困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上,这是相当新的困境。在中世纪的欧洲,上帝的感召是最基本的力量。在古希腊,照亮诸神的整个万神殿随时准备为你描绘适当的行动。像在“运动场上”的运动员一样,称之为你已经与世界融洽地协调起来,完全沉浸在世界之中,你不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然而,如果我们的文化不再是理所当然地相信上帝,我们还能够有荷马时代的好奇和感恩的心情,并被它们所揭示的意义所引导吗?我们的答案是,我们能做到。我们通过考察文学、哲学、宗教立论来重新展望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挖掘出了意义的古老来源,而且,教导我们如何每天重新发现我们周围神圣的、闪耀的事物。本书改变了我们对我们的文化、历史、神圣的实践和我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而且是很古老的——方式赞美和感激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的存在。我相信,中国的历史上也记载了这种看世界的相同方式。
问:这本书的出版是否意味着,您的研究在经历了从现象学到人工智能之后,又转向了对更加一般的人性问题的思考?
休伯特: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