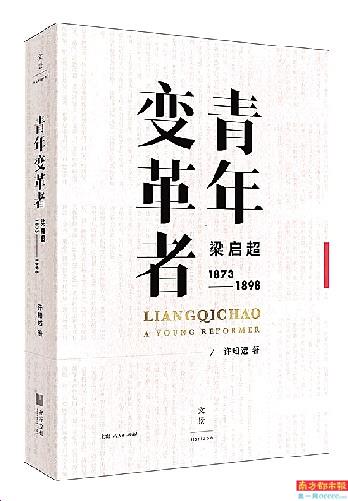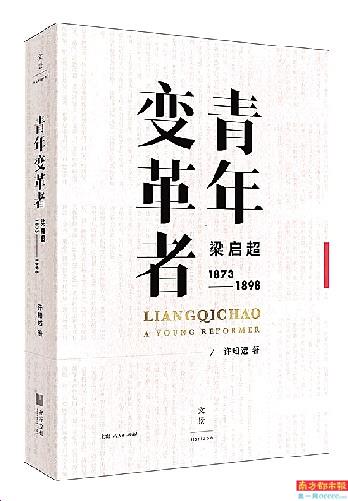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许知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68.00元。
□盛子胥
从关注现实到投向历史,作为知识人的许知远正在寻求自己的身份确认。尽管他的历史写作已有几年,但都不足以奠定其历史写作者的地位,更不能满足其写作的抱负与雄心。一定意义上,《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其角色转换的结晶——一方面,他要借此完成从新闻写作者到历史写作者的真正蜕变;另一方面,他自觉不自觉在梁启超身上寄予了很多的个人期许,甚至自我的投射。向这位100年前的思想先驱和前辈文人、新闻人致敬的同时,许知远也在无意中展示了当代知识人的困境。
相对而言,许知远选择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书写对象。作为晚清的言论界巨子,梁启超在一定的时间段是执舆论牛耳的人物;作为政治变革的倡导者和行动者,梁启超青年时期即介入政治,其后被各方势力所拉拢;作为学者,梁启超在生命最后十年左右才专心治学,涉及数量和门类却令人惊叹。比较一下许知远与梁启超,或许更有助于理解《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所呈现的青年梁启超形象。在志向上,无论梁启超还是许知远,都希望立功、立言;在追求上,两人都有家国情怀,都有自己的现实关切;在操作上,两人都关注天下大事;在职业上,两人都是新闻人和有影响力的知识人;在写作上,两人都是才子,文章有才气。但因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梁启超的才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现;而许知远虽然身处互联网崛起的契机,但抱负和才情未能尽数施展。《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的书写,是其正面强攻遇挫后的转向。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一部才子之书。它保持了许知远新闻写作的特点,全书文气充沛,纵横捭阖且起伏跌宕。其次,它信息量大,不仅描写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和经历,而且涉及了众多与历史人物和事件,勾勒出晚清知识人的群像。第三,本书的文字组织技巧高超,尽管引文甚多,但写作总体流畅易读。以上三点,都是本书明显的优点。
以具体的内容而言,许知远深得非虚构写作与新闻写作之长,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准备流亡为开始,然后追溯梁启超的出生、成长、求学及参加科举的经历。认识康有为并执弟子礼是梁启超思想觉醒的开始,他的目光从八股、辞章投向了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其关注范围也从中国转向了世界。几次会试不第虽然阻挡了他谋取功名的脚步,但却让他交游的范围大大拓宽,对于西方的知识也逐渐增加。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办的双日刊《万国公报》开始正式刊行,梁启超和麦孟华“试着充任主笔,负责论说文字”。这一尝试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三个月后,又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与汪大燮一起出任主笔。1896年3月下旬,梁启超来到上海,不久之后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一起创办了《时务报》(旬刊)。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采,几乎每期都有梁启超气势恢宏、文采斐然的文章。几期下来,《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发行量节节攀升,梁启超一举成为深具影响力的名人,其名声遍及全国。二十三四岁成名,固然让梁启超名利双收。但是,其知识不足的缺陷也很快暴露出来,1897年初,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称梁启超的文章放纵粗陋,不了解变革的逻辑。对于梁启超在《古议院考》中,称西方议院中国古已有之的说法,严复表示质疑,对于孔教,严复认为,“教不可保,也不必保”。这些犀利的批评,让如日中天的梁启超而言犹如当头一棒。
应该说,《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着意凸显了梁启超作为报人在言论上取得的成功,这一部分叙述较为充分。接下来,许知远还写到了《时务报》的内部矛盾,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经历。如果说,后面部分的内容因为利用茅海建等人既有的学术成果而比较准确,那么,对于梁启超与汪康年因为《时务报》过分成功而引发矛盾的叙述,则与马勇等学者的研究颇有出入。
在许知远的叙述中,报馆总理汪康年自认为出力甚多,但外界都将荣誉归于了梁启超。而黄遵宪规定的薪酬等级中,主笔优于总理。他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吃花酒,认为是联结网络、获取新闻的重要手段,但这一点却遭到指责。而梁启超则认为,汪康年兄弟主将将报务纳入己手,聘任人员也很少征求他的意见,自己不像是《时务报》创办人,而像供稿机器。此外,汪康年还对康有为的学说“颇多讥讽”。
相比之下,马勇2006年发表的论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中的研究,对于这一事情起因、过程和发展的描述更为客观、细致和准确,也更具解释力。
马勇的研究对于梁启超和汪康年之间矛盾的产生、势态的发展,以及双方之间的争夺和较量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展示了作为历史学者的史识和史料辨析能力。反观许知远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中的叙述,关于这一纠葛的经过和某些环节虽然也被提及,但是未能梳理出这一纠纷的要害和逻辑关系。在与此内容相关的第11章到第13章中,注释部分没有看到马勇的这篇论文。显然,许知远对于已经学术研究成果的利用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然不够充分,而他自己爬梳史料的能力不足,因此导致了这部分的叙述事实模糊不清。
而《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许知远受到康有为、梁启超两人自己的历史叙述影响太深,对传主的热爱使之与传主过于亲密,未能拉开合适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作出冷静的审视。在我看来,理性、冷静而客观的历史书写,较之“同情之理解”更为可取,因为前者可以提供更接近真相的史实,而后者很可能滑入价值观虚掷或事实不清的陷阱。就此而言,许知远的非虚构写作尚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