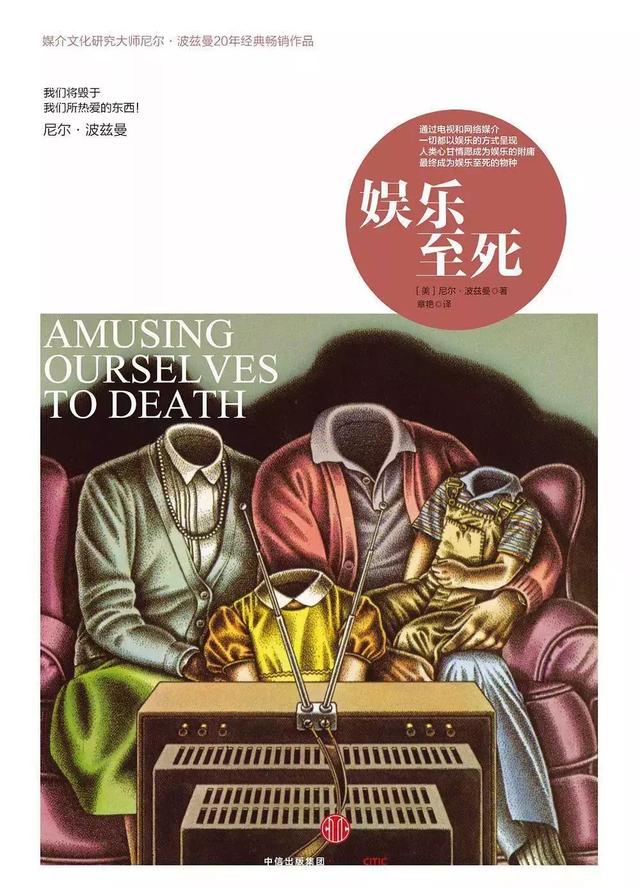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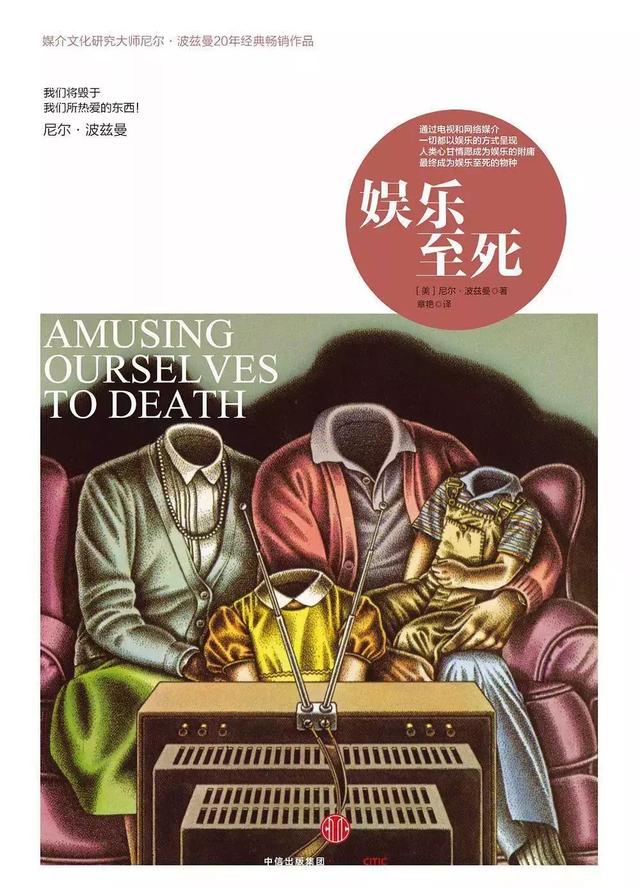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中,尽管首次将沉溺于强迫性电子游戏列为一种精神健康的特殊状况,但明确将参与游戏的时间、频率、强度等纳入考量范围,强调将时间标准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化因素,相关行为至少持续12个月才能确诊。尤其与网络游戏相关的“游戏行为失调”等概念,也依然处在科学论证阶段,并未最终确认和定性。而在最新版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虽然也提到了“游戏行为失调”,但也止于“有待研究”。不仅如此,在北美学界还出现了针对“游戏行为失调”等概念的抵制活动,认为不能未经充分科学验证就对其进行草率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11版《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
更何况,所谓“网瘾”,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精神疾病,而是已知的“冲动控制障碍症”在互联网使用者身上的具体体现。特别是从我国的具体临床经验来看,绝大多数被认定为具有“网瘾”的网络游戏用户,只是处于不适当使用的初级阶段,远没有达到瘾性疾病的程度。而且,在相关话语中,还隐藏着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偷换:就算真有“网瘾”这一回事儿——全互联网的锅,让网络游戏全背了——即不科学,也不讲究啊。
杨永信式强制电击戒网瘾治疗早已被卫生部叫停
所以,我们不妨坐下来仔细想想,究竟得是焦虑到什么地步,才会将“玩物丧志”“精神鸦片”这些来自1840年的历史结构的词汇,安置在150年之后的青少年身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呈现出周期性规律特征的道德恐慌背后的“救救孩子”,这些看似正义凛然的大声疾呼之中,到底隐藏着怎样不可名状的歇斯底里?
在这里,如果我们换一种叙述,或许能更有效地表达出这种不可名状的歇斯底里的社会代价。
杨永信在用电击“治疗”所谓的“网瘾”,进而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将其网戒中心的227个孩子,作为医学研究的受试者,以谋取其学术上的“成就”。截至目前,杨永信和其合作者,在中文期刊上共发表近60篇论文,有7篇论文发表在被SCI收录的核心期刊。
杨永信和其合作者的每一篇论文,都通过了医学界的相关伦理委员会和学术杂志的审查、审核。
图片来自《杨永信靠电人发了 SCI 和近百篇核心期刊?》·生物学霸·丁香园
那么,谁又该负这个责任?还有哪些人、哪些机构逃脱了法律制裁?
227个孩子以及更多尚未被社会知晓的孩子们,他们最宝贵的童年和青春,这个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
网络游戏火了,民科、民哲们也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由于我国的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家庭结构等多重社会结构的长期变迁和累积,以移动互联网为表征的媒介杠杆效应的持续性释放,再加上各类资本不断进场所卷携的新的商业模式,我国青少年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娱乐消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表达,也出现了多重意义上的过度透支。这些新现象、新症候,同电影、电视、文学、戏剧等传统文艺领域有着时代性的区隔,对于面向未来的文化治理,也同样是一项历史性的挑战。
但非常遗憾的是,我国的学术界、新闻界等领域的相关讨论,却依然停留在娱乐至死、乌合之众、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流行现象等上世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认知水平,相关理论、知识来源也局限于北美、西欧的有限著述和畅销读物,已严重滞后于当下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这种理论上、知识上的无能,为“救救孩子”“玩物丧志”“精神鸦片”“电子海洛因”“网瘾”等事实上的“民科”“民哲”话语,留下了可以兴风作浪的巨大空间。因为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20多年间,网络游戏治理之争,已然成为汇聚了各色“民科”“民哲”的“娱乐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异装癖”闪亮登场。对此,我国的知识界、新闻界要负相当大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