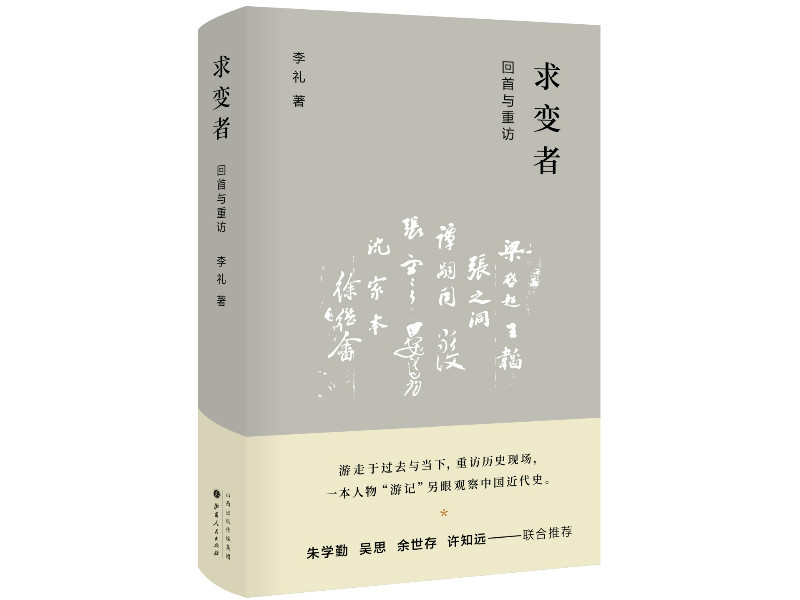撰文 | 徐悦东
新文化运动是否是对中国自身传统的一次断裂?中国历史的第三次大变革究竟是什么?变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该怎么看待“古今之变”?我们自己的文明在外来文明冲击之下,该如何安身立命?
7月5日,在“中西、新旧之间——近代史上的‘求变者’”沙龙上,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知名文化学者、作家余世存,资深媒体人、《求变者:回首与重访》的作者李礼和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与大家探讨了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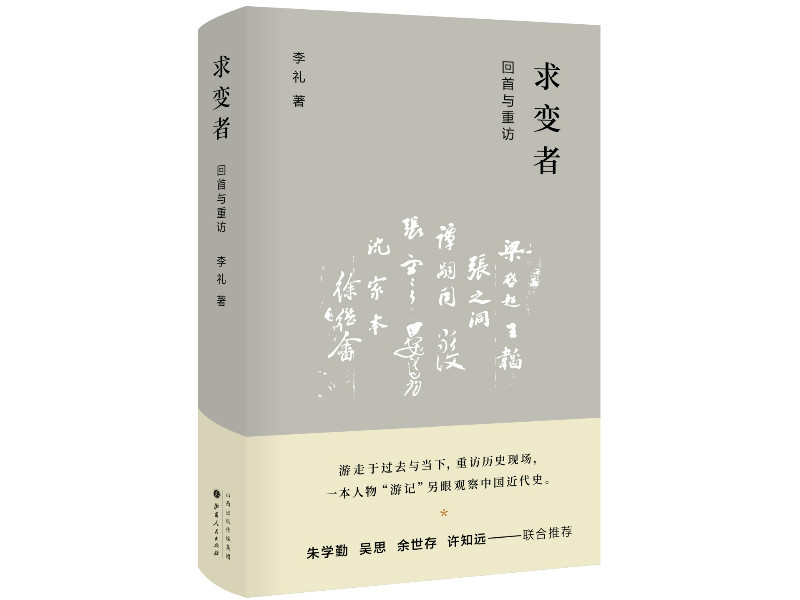
《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李礼著,汉唐阳光丨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新文化运动,并非传统的断裂,恰恰是传统的再现
余世存认为,五四有可能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明的一个节日。从五四到现在,我们历经了四到五个世代,而世代是看待历史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研究春秋的学者都知道,有所谓的所见世、所闻世还有传闻世,而对那个世代发生的事,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从儒家内部来讲,像重要的儒家学者钱穆,一直很痛恨胡适、鲁迅。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批人,使得人们所信仰的儒家在中国被连根拔起。但到了晚年,他却想明白了这件事情,他对弟子讲:不要责怪鲁迅、胡适,他们所有的言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新儒家的再现。
钱穆
余世存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学术公案”。作为儒家最正统的一位学者,钱穆在晚年承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流派,或者说,他想把五四纳入自家的文化。这就好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中国文化离家出走的叛逆之子,但经过了多年,这个儿子还是自家的。
当然,现在我们很多人依然觉得五四断裂了中国文化;而且,这种认识有很大的社会基础。当代有些人反而想回到那种遗老遗少的状态,回到我们以为的那种正宗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状态里面去:“假如五四是我们的曾祖、高祖辈,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反而没有先贤们那种开放的心理,没有他们那种现代的心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心灵已经封闭掉了。”余世存说。
比如说,我们该怎么看待梁启超?1929年梁启超去世的时候,还有一些人说,国民政府不应该对他有所表示。当然,另外一批人说,我们应该让国民政府给梁启超进行国葬。
从五四到梁启超去世,十年之间,梁启超在当时大家的心中,也面临一个角色的变化。因为他在五四那群人心目中,一直是在改良派阵营,甚至在保皇派的阵营里。但是,十年之后,余世存认为,新文化运动还是接纳了梁启超,甚至把他追认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而把胡适、鲁迅算作第二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
梁启超
在余世存看来,这个接续其实特别好,不然五四就是断裂了中国文化:五四跟康、梁革命还是一脉相承的。余世存认为,把梁启超作为第一代自由主义者是非常恰当的。
这是非常具有当代意义的视角。当然,有的人可以过成遗老遗少那样的生活,但其实我们大部分国民还是希望走入现代,希望跟西方交流、对话,甚至跟西方人打成一片。余世存认为,现代人已经在互联网上握手言欢,但我们在线下还在争论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巨大的分裂。
余世存还提到了龚自珍的意义。龚自珍被称为“中国的但丁”,因为但丁是马克思眼中的经典作家,恩格斯称之为“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个大诗人”。龚自珍也享有这样的地位。
龚自珍启蒙了谭嗣同、梁启超。梁启超说,在同治光绪年间,几乎知识界、学术界的人没有不提龚自珍的,甚至影响了几代人,一直到五四以后的中国人。余世存认为,他在诗中最重要的是流露出一个人的现代心灵。他的《己亥杂诗》影响了大家180多年。
余世存认为,我们在研究龚自珍的时候,就会发现五四不是断裂的。我们往前追溯,可以回溯到谭嗣同和梁启超;再往前追溯,就到龚自珍。这与“冲击—回应”模式的解释框架有所不同,龚自珍恰恰反映了这一切是自家文化水到渠成的结果,五四的变革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龚自珍会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家”。从梁启超到五四这几代启蒙思想家,他们的启蒙思想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延续了我们自家的文化传统,这应该是一个重新看待五四的新角度。
因此,余世存认为,钱穆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这说明五四不是一个没有受自家任何影响的叛逆之子,而是深深受到自家文化的影响,也知道自家毛病的儿子。所以,五四还是属于我们自家传统下的。
看待历史的变革,需要时间的尺度
余世存认为,时间也是研究变革的一个重要的角度。没有一种文化和制度能够长生久远,这也是看待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包括希腊、罗马的制度,都会走到它的衰败期。农耕文明的帝制制度,也曾经有过它巨大的合理性和好处,但是它后来也走到了衰败期。那么,在这种衰败期中,我们都知道需要变革了,那我们该怎么变?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余世存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作家,那些最敏感的心灵已经在琢磨这事。从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们知道这个古典的文化、帝制的文化,已经不能再安顿中国人的心灵——它需要变革。
就像龚自珍当年在己亥年去扬州找当官的朋友蹭吃蹭喝要钱时,他也感受到,虽然扬州非常繁华、富丽,但他知道这种文化、生活已经走到了末路。他的感觉很敏锐。在他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那篇文章里面,他很明确地说,从四时的变化来看,这个时候还只是初秋。
“所以,他说,在秋天,我龚自珍还不至于饿死,还能活着。或者,这个时代还能混着,他有这么一个预言。1839年之后,历史的任务就开始压给了曾国藩那些人。那些年他们一直在想,这种制度、这种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完?曾国藩一个有名的幕僚赵烈文就说,还有50年。他们对这个时代是有感觉的。”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大时间尺度来观察历史。不管是梁启超、王国维,还是五四这一代人,他们看到的问题所提供的答案,也并不是标准答案。他们一直把它当作体和用的问题,究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体用”关系,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争论。没有一个大的思想范式的转型,我们还是在这道题的陷阱之下进行思考。
余世存
余世存认为,文明的实践、文化的实践、历史的发展,正在给我们提供答案。年轻人的生活也在给我们提供答案。“现在年轻人眼里没有体用之说,没有说一定要以中学为体或者西学为体,没有说一定要有所谓的现代生活,有所谓的古代生活。我们现在的古典教育、西方教育,都是对我们心灵的一个很好的滋养。都是我们人生成长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能够寻找安身立命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年轻人那里,他们没有中西现代的那种分别心,说一定是中国文化救世界是很可笑的。”
因此,对近代史也好,对五四也好,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时间尺度来看。余世存认为,现在对近代史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在余世存看来,可能过了不久,我们还是会发现,五四虽然看起来撕开了中国文化,但从三百年的尺度来讲,五四还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第三次变革,需要怎么变?
马勇则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变革。殷周变革,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从原来混沌的组织方式,过渡到一个伦理架构的组织方式。在殷周之后,每个人都有姓。有了姓之后,就有了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五服之内不能通婚。这使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有了一个基本的章法。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解决了周王朝西周到东周之间的社会架构的无力。马勇认为,从周朝到秦朝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这样一种混沌的状态下,周天子发挥不了功能,只能找一个霸主。“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就慢慢诞生了,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联合国五常或欧盟。我们总要找到某种力量,出于正义去讨论问题,否则就没有任何正义可言。因此,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变。
那么,第三次大变革究竟是什么?变革的目标是什么?变革的前提是什么?马勇觉得,中国建立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状态下,我们把社会组织化方式、乡村架构、政府组织方式等,都发展到了极致。农业文明在帝制状态下构建了一个廉洁、简单的小政府。到17世纪早期,最早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来,就认为中国伟大得像希腊哲人所说的“哲人之国”。因为,当中国的科举制度成熟之后,文官制度等各方面的建构都非常好。
马勇认为,在两千年农业文明架构下衍生出来的中国科举制度、文官制度、贸易制度、市民社会的工商政策、外贸政策等,都是中国文明的早熟。“我读十六、十七世纪史料的时候,就觉得历史到这可以终结了。而且,当年的西方人也是说,历史就在这终结了不就可以了吗?全世界都能像中国这样,不就很好吗?一个皇帝在北京坐着金銮殿,我们每个人都在皇恩浩荡下生活,遇到某种委屈的话,还有士大夫替你说话,像现在美国的议员一样。”
马勇
但是,为什么后来出现一个“求变”的过程?到今天为止,这也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人类从大航海、大殖民时代迅速过渡到一个工业化时代。从18世纪中期英国引发的工业革命到今天为止,向世界的释放都没有完成。
而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有一个高度的伦理自觉。“我在研究五四的时候,举了几个极端的例子。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不论在村里还是到镇里,你敢随意和一个陌生人骂战吗?敢不敢骂?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总在想,我不认识他,但真打起来之后,他可能是我嫂子的嫂子的嫂子……总要找到某种关系。”
中国农业文明的状态是熟人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古典中国的社会形态中,法制不健全,而伦理的观念特别健全。只有建设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社会,我们才能脱离熟人社会。人们在一个陌生状态下,才有一个起码的规则自觉,完成工业化转型,我们才可以说与世界同步。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像王韬、严复等人讨论的近代转型的中国伦理价值转型。他们当时有很多困惑。当中国社会真的全部完成了向工业化转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碰撞,他们的问题也许就都能解决了。
“我们现在思考的所有问题,都是中西交流碰撞的问题”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从费正清开创以来的“冲击—反应”说有很大影响。虽然后面的第二代、第三代弟子做了很多修正,但直到今天,这个说法有相当的解释力。因为中国的历史如果没有进入到世界体系和东西方的文化、文明发展碰撞中,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发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量,即使不是一个绝对的变量。
李礼问许宏,“我记得曾经跟一个汉学家聊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未来会走向何处?他的回答很复杂,此外他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问: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他觉得没有所谓‘中国文化’这么一个东西。”比如唐朝、宋朝、元朝,那个时候各自的“中国文化”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化一直在分化、组合、融合当中。“他说的可能有点过激,但确实是一个重要视角。”
而在中西的碰撞之中,发生了所谓“古今之变”。到今天,许多学者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完成“古今之变”的国家,一只脚在古代,一只脚在现代。那么,“古今之变”我们到底完成了多少?在外来文明冲击之下,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中国到底是谁?
许宏认为,有学者曾经有这样的提法:我们现在思考的所有问题,都是中西交流碰撞的问题,几乎没有例外。考古学跟这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科学理性进来后,冲击了我们对三皇五帝、笃信不移的历史传承问题。我们就会思考,我们的历史有很多地方是建构的。在这种情况下,如胡适先生,把东周以上历史重新梳理,但中国历史的根就没有了。
许宏
那么,我们在有科学理性的同时,还要建构认同,就得先有一定的依据。而传统文献很难凭信,那么就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学就应运而生了。考古学是舶来品,是一门全新的学问,不是金石学的自然延伸。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在考古学诞生之初,都由本土学者来从事考古工作的国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考古,都是白人来挖。
这样的好处是,通过说文解字,我们可以建立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从而能够识辨甲骨文等古代文字。弊端是中国的考古融入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因素,甚至是民族信仰等问题。然而,在面对科学理性之时,中国考古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至今,仍是缠绕不清的问题所在。
许宏提到,现在网上许多人对自身历史有许多非议,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在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看中国。“我们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但我还是非常乐观地面向我们的现代和未来。农业文明跟工业文明有没有先进落后之别?绝对有,没有工业文明,根本没有我们的现代化。工业革命还没有结束,信息革命就过来冲击着我们。这些东西,使得我们意识到必须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双重道路,这也是全球化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根本接受不了‘回到宋朝’,你能接受得了没有电灯、电话、手机、飞机这样的时代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马勇老师说的,我们还在社会转型的潮流中。其次,像余老师刚才讲的,年轻一代没有‘中西之别’了,这太有意义了。”
许宏想起了许倬云和龙应台都说过类似的话:最值得尊重的,是每个人的个体和全人类整体,而中间的许多建构、组合、组织,都是不太真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从比较长的时段来看社会和文明,而考古学恰恰是这样。考古学最不擅长的是,对具体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人物、绝对年代的把握;但考古学擅长的是,长时段地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观察。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安也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