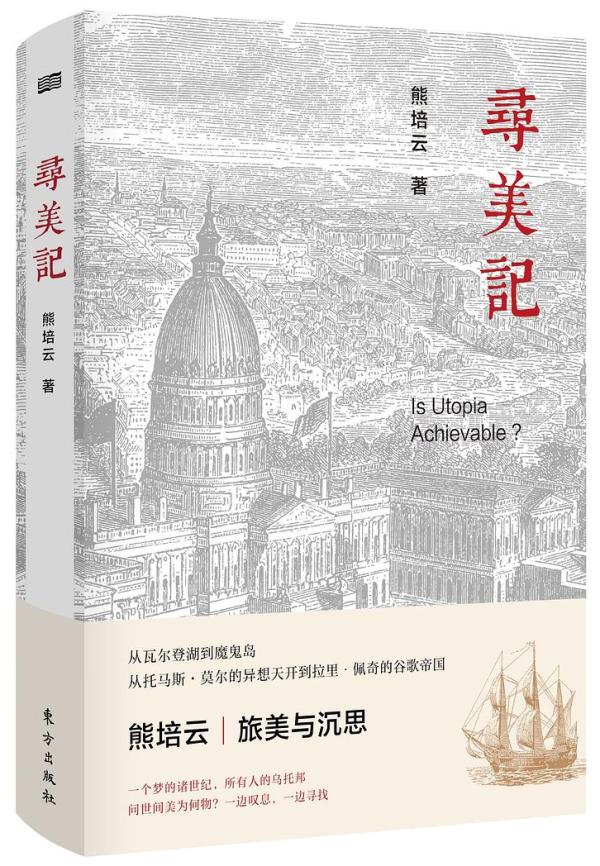人类历史上的诸多乌托邦实践最后之所以作鸟兽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轻视了人性中的幽暗。
——熊培云在新书《寻美记》中如是说。通观全书,他也是带着对乌托邦的学术思考来观察美国社会的。所以这本书看上去是美国游记,但一半的篇幅都在讨论乌托邦。封面印有英文书名: Is Utopia Achievable?(乌托邦可实现吗),更像是这本书的副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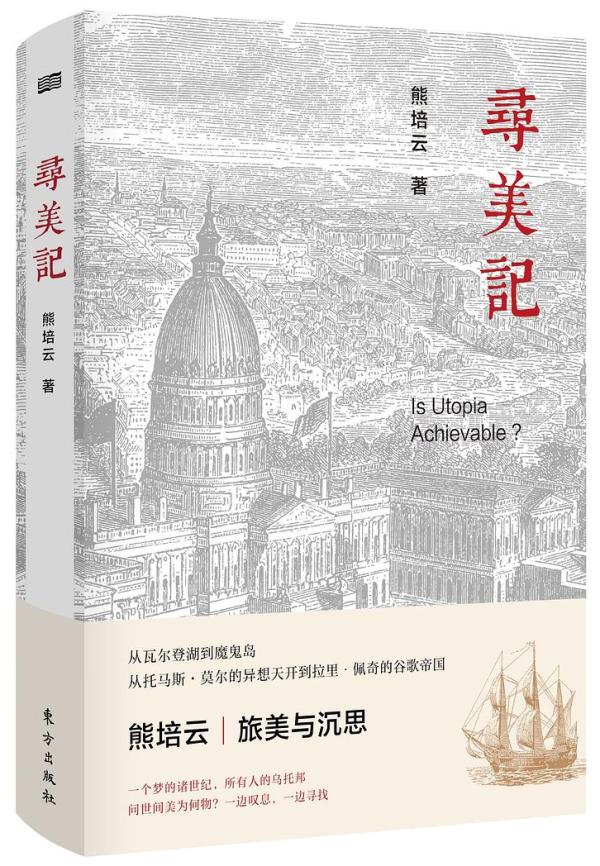
《寻美记》
在该书的第一章中,熊培云对比了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的美好国家和美国的相同之处,其中包括“以农立国、一夫一妻制、重视思想和科学、尽可能在海外作战、标榜王师与人道主义”等十五条。在之后的章节中,他还讨论了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小说《太阳城》、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及扎米亚京的《我们》等多部著作以及与美国和想象世界有关的影视作品。
无论对于美国社会还是乌托邦,熊培云在书中都流露出深刻的理性思考,比如他讲到“作为一个建立在近现代观念上的国家,直到今天,美国也没有真正实现其所标榜的平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种子发芽、理想实现需要时间;另一方面,这也与人性的自我设防有关。柏拉图说,灵魂有多少种形状,国家就有多少种形状。”
熊培云(左)和东方卫视首席记者、主持人骆新在对谈现场
在序言中,熊培云对“乌托邦难以建成或易于功亏一篑”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包括“一,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二,乌托邦的相异性与人类追求的不确定性;三,人性的迷局与人的不可驯服性;四,人类的非完整性;五,人类生活的结构性;六,技术发展的不可逆性和风险积累。”
由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围绕乌托邦的相关问题对熊培云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全文。
澎湃新闻:
您在《寻美记》中同时介绍了很多乌托邦文学。为何要将乌托邦作为这本书的副线?
熊培云:
乌托邦(Utopia)这个词虽然来自英人托马斯·莫尔,但它连接的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贯穿人类生活始终的。过去这些年,无论是在大学教课,还是平日写作,我对乌托邦及其研究本来也投入了很大的关注。而我在《寻美记》中谈到很多与乌托邦有关的章节,最重要的原因是读了鲍德里亚的一个小册子《美国》。鲍德里亚说美国是托马斯·莫尔意义上的一个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不过他没有细陈缘由。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于是回过头来又仔细读了几遍《乌托邦》,找寻相似性。而且,在我梳理早期美国史的时候,我注意到,美国的诞生同样得益于出现在“新大陆”的各种乌托邦实践,那里有那种我以前谈到的“市场政治”的东西。
《美国》
澎湃新闻:
您在书中也有关注乌托邦关于两性关系的规定。为什么乌托邦倾向于在这方面做出规定?
熊培云:
性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它不仅涉及人类的生息繁衍,而且事关社会构成以及审美的激情等等。当然,它同样关系到人的思想自由与身体自由。所以,在《一九八四》里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在《太阳城》里也有相关严苛的规定。此外,对性的控制还有可能直接关系到权力的分配,比如我在《寻美记》里提到美国的一个乌托邦社区,社区负责人可以有多于其他社员的性交权,有的社员甚至因为洗脑而被变相剥夺了性交权和生育权,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射精是有害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乌托邦设计在两性方面都违背人性。
澎湃新闻:
莫尔的《乌托邦》沿袭了《理想国》中的公有制,这同美国奉行的私有制截然相反。据您的思考,理想的政治社会为何总是倾向公有制?公有制或私有制是建构美好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吗?
熊培云:
回顾过往的种种乌托邦设计,它们想要提供的大多都是集体幸福的解决之道。理性层面,公有制因为表面上更具有计划性和高效率所以广受推崇;感性层面,公有制也符合人类在心灵上的对平等世界的要求。然而,在这里人的本性和人的意义性都被忽略了。同样,一个人是否幸福,首先取决于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他客观上正在享受的所谓公有制。美洲大陆早期的诸多乌托邦实践中,也有实行公有制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也多不了了之。
公有制和私有制其实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最有效的是互为救济,同时为民众所用。一方面,国家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国民的整体利益,比如制定怎样的法律保卫公民的利益,它追求的是有效。而其他具体的利益,比如一头牛卖多少钱,则由个人说了算。简单说,涉及公权之处当为公有制,涉及私权之处当为私有制。简单说,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它们都是美好社会的必需品。关键在于恰到好处,用对地方。
澎湃新闻:
不管是书中构建的乌托邦还是现实政治中的乌托邦实验,似乎都有“极权”的味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乌托邦应该如何处理“人性之恶”的问题?
熊培云:
有一点要承认的是,由于违背人性,或者超出了人的理性范围,过去两百年间有许多乌托邦实践走向了它的反面。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反乌托邦小说的问世。在那里,乌托邦似乎成了“极权”的同义词。
其实,乌托邦并不必然意味着极权。欧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人试图建立的乌托邦,从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极权主义的影子。人类社会,实际上也是从一个破碎的乌托邦走向另一个破碎的乌托邦。至于为什么是破碎的,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所谓的“人性之恶”,还样要看到人类理性之局限。人类最大的理性不在于认识世界,而是认识自身。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格拉底。他说他比别人多知道些的东西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换句话说,在洞悉人类的无知方面,“知无知”的苏格拉底不愧为先知。
澎湃新闻:
您在书中表达了在科技构建的乌托邦里,乌托邦的价值会压倒人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可能威胁吗?
熊培云:
从本质上来说,乌托邦只是人类为自己设计的器物,其价值不应该高于人类本身。否则,就意味着人类的主体性的丧失。“玩物丧人”显然是比玩物丧志要严重得多的事情。
至于AI,就像核武器在二十世纪被发明一样,人工智能同样只是人类知识的延伸。它可能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带来坏的结果。聪明的爱因斯坦有能力推导出E=mc2这个深奥的公式,却无法用这个公式计算人类深不可测的未来。
澎湃新闻:
您在书中谈到梭罗和《瓦尔登湖》。其实不管是乌托邦还是现实世界,都会遇到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但为什么到了21世纪,人们似乎在现实中建立乌托邦的兴趣变淡了?
熊培云:
梭罗对乌托邦建设中的集体主义是保持警惕的,所以他宁可孤独地坐在一个南瓜上,也不愿去附近的乌托邦社区里生活。而乌托邦之所以无法建成,或者说注定是破碎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也在于人类虽有共性,但也有千差万别,因为每个人有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都有赋予意义的能力和趋利避害的本能,这都不是集体主义的产物。
瓦尔登湖畔,梭罗的背影(熊培云 图)
而且,就自身而言,集体主义也意味着在特定情境下的某种平衡或妥协,当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原有的集体主义就会被逐渐打破,而走向新的集体主义。在此意义上,集体主义是好是坏,还要看它被赋予怎样的价值。通常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将民主视为集体主义,而自由视为个人主义。如果不保卫个体自由,民主也会失去应有之义。
今日世界,集体主义的乌托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式微。不过,借助科技之力,许多人开始藏身于个人主义的乌托邦里。
澎湃新闻:
巴黎和纽约能否算作“艺术的乌托邦”?以您自己在两地的经验来看,“艺术的乌托邦”是不是最理想的乌托邦?巴黎和纽约的经验是否可以复制?
熊培云:
自古以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至少有这两套乌托邦话语:一是政治的,二是文艺的。举例说,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试图建立的是一个政治乌托邦,在那里人分为几等,各安其志,各司其职,有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意味。而且,在那里包括诗歌与绘画等文艺是被贬低的。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一切艺术创造都是对世界的拙劣的模仿,会影响雅典公民对理性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是理性的产物。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理性如果被拔高为独一无二,甚至统领千秋万代的真理,并且试图通过暴力来推行,则有可能走向理性的反面,直到堕入疯狂的境地。这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之所以兴起以及现代性滑向大屠杀的大背景。为此,许多学者都做了深刻的反思。
另一种是文艺的乌托邦,或者您提到的“艺术上的乌托邦”。它所连接的更多是个体的经验和感性。相较于政治乃众人之事。我宁愿相信后者首先是个人精神世界的产物。就像托马斯·莫尔与陶渊明,他们笔下的乌托邦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害的。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嘱意或者生产适合自己的乌托邦世界。两相对比,如果从现实角度来看,政治乌托邦事关众人,因此需要互相妥协,以期众志成城;而艺术乌托邦事关个体,因此需要互不干涉,达到各美其美。
纽约和巴黎有很多艺术品,但那只是器物。如您所知,乌托邦的价值不在器物,乌托邦里也不只有器物。回到我上面的理解,在今天相对开放的世界里,很难说哪个地方是艺术乌托邦,因为艺术从来不属于任何地方,而在于它们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所以我们更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现实之外,你的人生是否另有维度?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艺术乌托邦?
澎湃新闻:
您在书中引用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的“美国有良好的乡镇精神和地方自治传统”。您在书里也讲到一些事例,能否再进一步总结一下美国的乡镇精神何谓?
熊培云:
按鲍德里亚的说法,美国是欧洲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如果回溯早期移民史,不难发现,如果具体到可以“发射的人”,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而早先到达的清教徒,也是各行其是,建立了不同的殖民地。最初只是一些小型社区,有幸生存下来的,逐渐建立起市集和乡镇。慢慢地,才有了后来的州,以及作为美国雏形的邦联。这种从个人到地方再到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可以说是新大陆的优势。所谓乡镇精神,本质上说也是地方自治精神。在不违背联邦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文化认同,美国至今仍在努力维系这种社区自治传统。前者,总统不能免去州长或镇长的职务;后者,比如我在书中提到的阿米什人,他们可以在宽松的氛围中努力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免受外界干扰。
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一角
澎湃新闻:
您留学的地点选在欧洲而非美国。美国之行加上《寻美记》的写作,如果让您重新回到过去,您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会对您的人生产生不同影响吗?
熊培云:
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但即使是回到过去重新选择,每个人也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道路。所以我说“你是你的沧海一粟”。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我们人生的可能性是沧海,而最后能够完成的,却不过是沧海一粟,万千可能之一种。
回想我当年在巴黎读书时的收获,我依旧认为是非常值得的。它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是走向今日之我的桥梁。如果早先能去纽约、伦敦或其他地方留学,也未尝不可。人生原本是无穷的未知,走着走着,终了留下两行时深时浅的脚印。倘使早先做了其他选择,自然有其他不同的脚印。
我唯一能够控制的是既然已经做了选择,就善待自己的选择,认认真真地走,而不必劳神在万千可能中哪两行脚印是我必得的。无论走过怎样的道路,见过怎样的风景,遭遇了怎样的一群人,有朝一日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恐怕都难免像先贤苏东坡一般感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