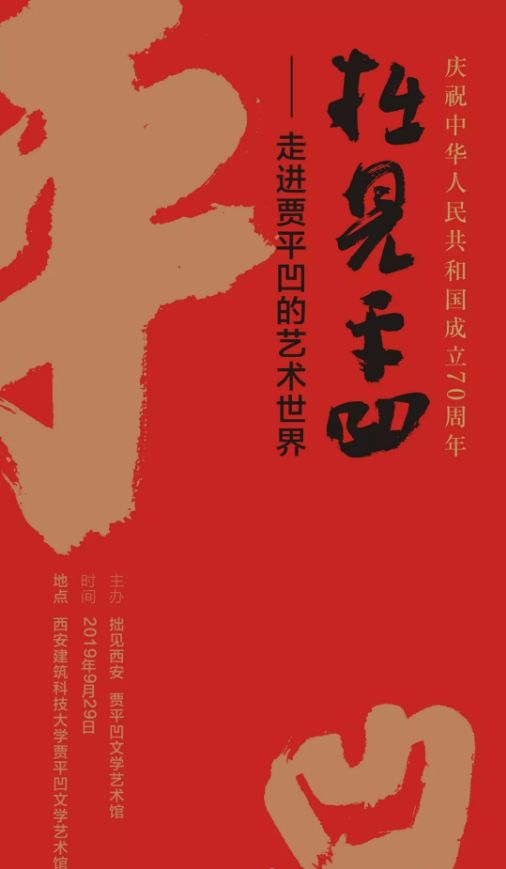总第一六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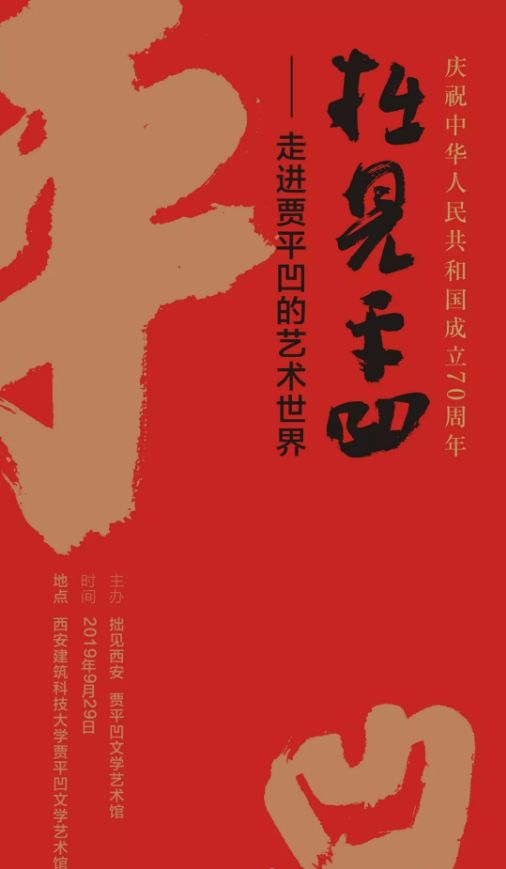
拙见平凹——走进贾平凹的艺术世界
主办: 拙见西安 贾平凹文学艺术馆
时间: 2019年9月29日(上午十时)
展期: 2019年9月29日-11月10日
地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贾平凹的书画好不好,值不值,都来说说看......
延伸阅读
郎绍君:贾平凹书画读看散记
前些年,我去西安开会,曾与陕西画家邢庆仁造访贾平凹,见到他的书画作品和古碑雕刻收藏,知其在文学创作之余,写字作画,玩赏古物。又知其有时参与画家活动,且有论评画家的文字。他的《书画创作年表》记:80年代中期开始写毛笔字并接触绘画,约十年后,书法进入市场,兼任太白书画院院长,相继在西安、苏州、上海、成都等地举办书画展,出版书法集、画集、书画集。说:“我是先文学,后书法,再后绘画。”文学写作是他的“职业也是事业”,书画是他的“余事”——“作为陶冶自己心性之道,更作为以收入养文养家之策。”
贾平凹作品
贾平凹没有拜师学画的经历,没进过美术学院,他的画与学院画和传统文人画都不同。美术史上的“文人画”,是指唐宋以来具文人身份与修养、讲究笔墨形式和文人意趣的绘画传统,有文脉可寻,有大师级人物。陈师曾称赞说:“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轻妄之辈的能望其肩背哉!”贾平凹是杰出的作家,其学养可与出色的传统文人相比肩。他说:“在我的认识里,无论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除了不可替代的技外,其艺的最高境界都是一样的。我常常是把文学写作和书画相互补充着去干的。且乐此不疲,而相得益彰。”贾平凹的小说,从多角度描写近百年来农村的变迁,乡人的悲欢离合种种际遇,人性的伸张与扭曲,进而又开掘城市人生的“废都意识”,其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吸纳明清白话小说,“形成自然、含蓄、富内在韵味的格调。”(洪子诚)也许可以说,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正是贾平凹书画创作的底蕴——有赋予作品独到精神内涵之能力。譬如:
贾平凹《曹雪芹图》
画一株树,两边一僧一道。题“忘却烦恼即真如”——佛家谓“真心”“佛性”为真如。贾平凹的画,以独到的图像表现了佛道相通的劝诫。
画一虎驮佛,名曰“陀佛”。题:“唐僧取经之过程,其实是伏魔之经历。取经以诚,伏魔以力。”——以有趣的画面、有趣的文字解释唐僧取经,端的是有得之思。
画一辟邪样神物,题:“佛为魔生,魔为佛存,不足以奇。”——从另一角度隐喻了佛与魔、善与恶的关系。
画一人骑在鱼背上在钓鱼,题“骑鱼钓鱼图”。——这和“骑驴找驴”是一个意思,幽默中透着智慧。
画一人伏虎背读书,题“骑虎读史,披花诵经”——读史者儒,诵经者释,儒释相合。这也是以书画喻理的一例。
画女上衣,中插一花,题“服装与花”——双重比喻,令人想到人与衣饰、文与质的关系之类。
画一人穿战国衣,姿态如稻草人。题“穿一件战国时期的衣裳,是什么样儿?”——以衣装的时代错置,喻类似的可笑现象……。
贾平凹《两棵树》
这些作品,简而有谐趣,图文互解,传达着人生智慧。文发于画,画与文合,其意又非文所能诠释。《贾平凹书画作品选》收入243幅作品,涉及佛道的就有30余幅。这让人想到他在《带灯》中塑造的女主人公,“镇政府干部只是她的外衣,她的内心是靠近佛的”, 她的“全身都放了晕光”。评论家也发现,带灯这个形象“放弃了道,从儒转向了佛,只是似儒非儒。”(陈晓明)这表明,平凹小说人物的精神形象,与他的佛道人物画是连通的——他是把作家的人生经验与感知,移入了绘画。这是一般画家所做不到的。
节选自郎绍君《贾平凹书画读看散记》
《贾平凹书画集》自序
贾平凹于1998年3月5日
这一本书画集,书多画少,可以说是本书法集,收辑了近几年所写的一部分,但我却是从六岁起至现在几乎天天在写字,以字活人的人。如果在古时,一个写字的人是不会出一本书法集的,他们的任何一位也比我在这本集中的字写得好,然而现在,我却是书法家,想起来委实可笑。苏东坡是我最向往的人物,他无所不能,能无不精,但他已经死在了宋朝。我的不幸是活在了把什么都越分越细,什么里都有文化都有艺术的年代,所以,字就不称之为字,称书法了。食之精细,是胃口已经衰弱,把字纯粹于书法艺术,是我们的学养已经单薄不堪。越是单薄不堪,越是要故弄玄虚,说什么最抽象的艺术呀,最能表现人格精神呀,焚香沐浴方能提笔呀,我总是不大信这个。庙里的大和尚,总是让乡下的老太太在佛像前磕头烧香,但他们知道佛是什么,骂佛是屎瓶子。
我喜欢写字,是我从事着写文章的工作不能不写字,没有当兵的不爱武器的。
我看到过许多人,以至于许多人让他的孩子,没黑没明坐在房子里练字,我就想起了乡间剪窗花的妇人和日本人的相扑,有趣或许有趣,但毕竟过去了。我坦自招来,我没有临习过碑帖,当我用铅笔钢笔写过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后,对汉字的象形来源有所了解,对汉字的间架结构有所理解,也从万事万物中体会了汉字笔画的趣味。如果我真是书法家,我的书法的产生是附带的,无为而为的,这犹如我去种麦子,获得了麦粒也获得了麦草。
有人说,书法必须是毛笔创造的。这话若被肯定,那么,我的字被书法了是八十年代的中期。那时,我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从此一发不能收拾。我的烟也是那时吸上瘾的。毛笔和宣纸使我有了自娱的快意,我开始读到了许多碑帖,已经大致能懂得古人的笔意,也大致能感应出古人书写时的心绪。从那一阵起,有人向我索字了,我的字给许多人办过农转非、转干、调动的好事,也给许多人办过贿赂、巴结、讨官的坏事,我把我的字看得烂贱如草,谁要就给谁写,曾经为吃得三碗搅团写过一大卷纸哩。
但是,被人索字渐渐成了我生活中的灾难,我家无宁日,无法正常的读书和写作,为了拒绝,我当庭写了启事:谁若要字,请拿钱来!我只说我缺钱,钱最能吓人的,偏偏有人真的就拿钱来。天下的事有趣,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能以字易钱,我也是爱钱的,那我就做书法家呀!
在我有了做“书法家”的意识,也可以说有了‘书法家”的责任,我认真地了解了当今的书风。当今的书风,怎么说呢,逸气太重,好像从事者已不是生活人而是书法人了,象牙塔里个个以不食烟火的高人自尊,博大与厚重在愈去愈远。我既无夙命,能力又简陋,但我有我的崇尚,便写“海风山骨”四字激励自己,又走了东西两海。东边的海我是到了江浙,看水之海,海阔天空,拜谒了翁同龢和沙孟海的故居与展览馆。西边的海我是到了新疆,看沙之海,野旷高风,莫把冰山与大漠。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在这两个海边的日日夜夜,当我每一次徘徊在碑林博物馆和霍去病墓前石雕前,我就感念了两海给我的力量,感念我生活在了西安。
《相马图》
我最清楚不过,我的书法是缺乏基本训练——而这又是当今流行的一种要求——它充其量属于顿悟式,这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实行民选一样,民选是民选了,却常有军人们起来就把民选的总统颠覆。我也明白,我的书法多多少少借助了我在文学上的声名,但我想,这和那些领导的题字还是两码事吧,所以,才敢于让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
但我仍坚持,我写的是一些汉字,不是书法,我也不要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