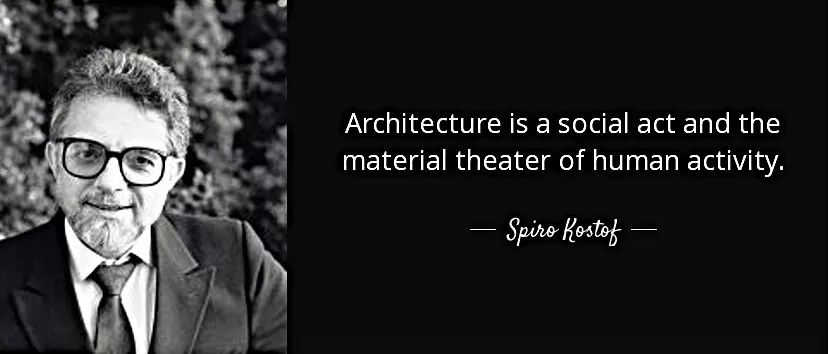作者:
【美】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1936—1991),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代表著作有《一部建筑史:场所和礼仪》(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Settings and Rituals)。
译者:
冯晋,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本文摘自“文化与人造世界 —— 建筑史的限度”,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8月刊,总第200期P122-130
摘要:斯皮罗·科斯托夫(Spriro Kostof)1988年在密歇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这篇讲演是对自己革命性学术生涯的一次总结,讲述了他从求学耶鲁大学到执教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不断变化的心路历程、与其相关的学术环境以及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他对西方建筑史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反映了20世纪后期美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发展变化以及在建筑史学和史观上的突破。他提出建筑史不应限于对过去建筑形式风格迭代的研究,而应成为人们为改善未来生活环境而争辩的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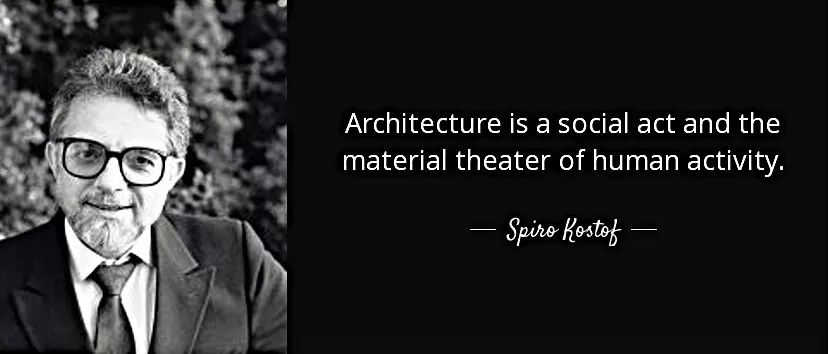
▲“ 建筑是上演在人类活动物质舞台上的一出社会戏剧。”
——斯皮罗•科斯托夫
一、两篇不比寻常的新著述
为了准备这次讲课,我重温了这二三十年来建筑历史的著述,发现自己在这文献的海洋里不时地重复感到两篇著述的重要性,它们发表不久而又不比寻常。尽管意图和视角不尽相同,这两部著述都承认我即将讲述的故事中事件的重要性。通过这个故事,我将试图在我们这有着百年历史并令人尊重的学科中加入个人的视角。在建筑历史的文献中,我经常想到的是约翰·马斯(John Maass)发表在建筑史正式学科组织会刊《建筑史家学会会刊》1969年3月号上的文章《建筑史家之不敢涉足处》和牛津大学1977年出版的戴维·沃特金(David Watkin)的著作《道德与建筑》。
马斯分析了《建筑史家学会会刊》在1958年到1967年这10年中发表的论文,告诉我们,建筑史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注意力放在了西方纪念性建筑上,而其中又对美国情有独钟,在关于欧洲的文章当中,则偏重英国、法国、意大利,这简直就是18世纪建筑学子们所必经的欧洲之旅。马斯指出,工业建筑被忽略了。而作为常规,这10年间发表的建筑史研究中,大部分对高大上建筑的研究都将其当作孤立的作品,并没有融入更大范围的物质和文化文脉中。
沃特金的书大体上被看成是对那时还被人们尊崇的建筑史家、偶像级前辈——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的攻击。沃特金记述了佩夫斯纳如何披着“功能主义”外衣,用一种巫毒教咒语的方式重复着时代精神理论的说教,建立了排斥一切的和专制的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的信仰。沃特金指出:“佩夫斯纳的观点是整体论的,并且是一心只想未来的;他强调艺术和建筑必须服从政治和社会的准则。因而他强调可以根据他对政治和社会的理解而得知当今时代必然的建筑风格。”
马斯和沃特金的非比寻常之处在于他们对建筑史学这一一贯忽视自省的学术领域的视野和方法提出了质疑。建筑史学的第一部发展史刚刚在1980年由沃特金写成,题为《建筑史学的兴起》。时至今日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书评读起来就像是老师的评语 —— 这方面很好,那方面还不够,有这些缺漏,有那些失实;而对作者作为建筑史家的基本出发点、立论依据以及政治立场却不置一词。这个问题若与其他学科相对比就会更明显。比如在城市地理学界,每篇论文在开头都会有一段关于方法论的说明。
二、建筑史是什么,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
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早就知道建筑史是什么,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那就是大写的建筑——即在从迪朗(Durand)、皮金(Pugin)以及其他19世纪先驱者以来分化得越来越细的风格分期中被谱系化了的建筑物。如加洛林时期(Carolingian)、奥托时期(Ottonian)、前罗马风时期(Protoromanesque);或者木架风格时期(Stick style)、雨淋板风格时期(Shingle style)、安女王时期(Queen Ann)。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建筑历史所描绘的景观看起来极为怪异,就像著名画家斯坦伯格(Steinberg)笔下从曼哈顿所看到的美国[5];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和建筑大师高耸于原野之上,与其相应的则是关于这些建筑和大师的专著。在那里还有领地的划分,外人不可擅入。如果大家都知道某某人正在研究斯派尔大教堂(Speyer Cathedral)或者克吕尼修道院(Cluny),别人就不可再染指这栋建筑。相关研究成果或许要等数十年才会发表,一旦发表,我们就会终审般称其为这一个案的经典,意即任何对该建筑重启研究的企图皆属不智。
我们非常关心建筑师的个性与特点、建筑设计的年代以及渊源关系。感谢上帝有像约翰·菲辰(John Fitchen)或卡尔·康迪特(Carl Condit)那样有工程学背景或建筑实践背景的人替我们搞定有关建造的问题,我们都为此庆幸。我们都曾尝试过讨论建筑意义,一方面依靠类似图像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则靠不知羞耻的臆测——即类似“事情或许并非不可能如此”这类在其他学科中难以成立的推理。当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许才能见到一本像奥托·凡·希姆森(Otto von Simson)借助各种人类知识去解密重要建筑——类似贾斯廷时期(Justinian)拉万那(Ravenna)或哥特大教堂——含义那样的精彩著作;这种书仅以其博大精深就令批评家难以置喙。
除了偶然触及营造,所有这些建筑史研究的方法都执迷于最终建成的建筑物本身,而对设计和建造过程漠不关心。公平地说,我们都是偏重结果而轻视过程。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是谁出资建造,在建成的建筑物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谁因其建造而获利或蚀本,建筑地段过去有什么又如何到手,建筑材料来自何处,建筑师受到了怎样的压力,又在何种程度上左右了建筑的造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所研究的建筑物从本质上视为艺术品,就像绘画与雕塑一样。想到建造需要复杂的技术和劳动组织,想到建筑物需要达到某种目的和满足一定的功能,想到建筑物原初的用途和用户会在使用中随时间变化,我们就会感到不胜其烦。我们视建筑师为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艺术家;视他们的每件作品为独一无二的杰作,超乎坚固适用的俗谛而进入了审美与文化的境界。
我们这些皓首穷经于这个象牙塔中的史家大抵雷同。我们所学的是对建筑形式的视觉分析与品评,从空间到外观;用的是从里格尔(Riegl)、沃尔夫林(Wӧlfflin)、凡·希尔德布兰德(von Hildebrand),以及佛西隆(Focillon)等人的理论杰作中提炼出来的方法。这些大师们精研细磨的论说早已沦为纯粹的习惯性操作。我们学风格就像学外语,生硬而不精确。而含义、象征与图像志则是另一套语言,易学而有价值,生动而更像故事。我们一些胆大的史家接纳了无意义空间存在的可能,并以突破这些禁忌为傲。假如大家真的听说过阿道夫·格勒(Adolf Gӧller)其人,我怀疑谁都可以根据他的《建筑美学》来建构一套达到这一效果并令人信服的立论。
从一座历史建筑物中总结出风格和意义不应附加任何个人观点;实际上个人倾向表现得越少越好。我们一直被要求做到客观。如果我们必须承认受到某种理论的影响,那大概就是实证主义了。我们模糊地感到,在形式与意义之外,还有其他的探索方向。但在我们奉为楷模的小群体中,还没有人鼓励我们去探索。因为有政治偏见的味道,并且还有人们认为与纯艺术想象无关的因素,阿诺德·豪泽(Arnold Hauser)的《社会艺术史》受到质疑。另外,他关于“没有人名的艺术史”的言论听起来有点像煽动。
时代精神(Zeitgeist)是个很不好的概念。它是来自黑格尔主义思想的产物,在我们的话语中根深蒂固。它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直接表现在人类知识和活动的每个分支,在艺术上尤为突出。自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以来,几乎所有的建筑史家都相信,将建筑视为文化的表达形式是一种必要的能力。拉斯金在1849年写道:“所有的建筑都是某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历史及宗教信仰的某种体现。”从巴尼斯特·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开始,建筑通史的前言中都有类似观点的陈述:“建筑是各个时代的印刷机,不断印出社会状况的历史。”
忽视这一必然规律的建筑师将要自己承担被建筑史家贬为时代精神背叛者的风险。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就正是这样将大多数19世纪的建筑大家一笔勾销。佩夫斯纳(Pevsner)也为此而嘲笑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高迪(Gaudi)以及表现主义者;在其晚年,佩夫斯纳又将南美建筑师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和菲利克斯·坎德拉(Felix Candela)等人的作品贬为“满足建筑师个人表现欲、大众猎奇心理和逃避现实的结构杂技。”
那么如何平衡我们对建筑的造型和对成为永恒艺术品的迷恋,以及决定论者对建筑必须反映当今与未来时代的要求呢?这很不容易,如我前面提到的,因为这是一个不爱自我检讨的学科。这里一定要提及吉迪恩的公式,建筑在两个层次上存在;一是作为各种因素所决定的产物,“但一旦形成就有了自身的活动组织,有着自己的性格和后续生命”,从中可以抽象出宇宙的原则。所以你可以有你的德沃夏克(Dvorak)和你的佛西隆,你可以认同《艺术史作为一种精神历史》和《形式的生命》。
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我在耶鲁大学艺术史系作学徒时的思想氛围。我们以受到法国的影响而著名——佛西隆、奥伯特(Aubert),等等—— 并且我们还有着对形式问题的执念。占据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德国人轻蔑地把我们称为“那个形式主义学校,” 那些人好像是一种用弗里德兰德尔(Max Jakob Friedlander)、克劳特海姆(Richard Krautheimer)和维特克沃尔(Rudolf Wittkower)混合出来的霍尔蒙克斯(Homunculus),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探索内容问题和珍贵、详细的历史档案材料。
当时的几个项目和名声维系着耶鲁。杜拉欧罗普斯(Dura Europos)归我们做,当考古学家们在努力清理挖掘现场和重建洗礼堂,位置就在学院路由路易斯·康设计的新美术馆中,隔壁的我们则正在根据“自然形体在空间中的视觉效果”来区分希腊化时期人们对世界的描绘方法和以杜拉遗址基于抽象的和平面化设计为代表的闪米特描绘方法。
在海街(High Street)艺术史系另外的项目中,厉害的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通过系列学术讨论和像《玛雅建筑空间设计》那样的精彩论文,正在从考古学家的统治下重新占领中美洲。萨姆纳尔·麦克奈特·克罗斯比(Sumner McKnight Crosby)夺回了圣丹尼斯教堂,这可以说是一场“那个形式主义学校”的大政变,因为那实际上是一个你可以记录一个风格的起源的案例,而且正是哥特风格如日中天的1144年,小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Jr.)完成了关于努瓦永(Noyon)的著作,开始着眼于佛罗伦萨大教堂杏仁门上的雕塑。我记得有成百上千耳垂和鼻子的黑白照片,要我们辨别出哪些是乔万尼·达姆布罗吉奥(Giovanni d’Ambrogio)的作品,哪些是皮埃罗·迪·乔万尼·泰代斯科(Piero di Giovanni Tedesco)的作品。这叫作“视觉训练”。于是我们偷了验光师店里的有这几个字的标牌安装在我们讨论课教室的门口,我们觉得这很有意思。
然后就是激情澎湃的文森特·斯卡利(Vincent Scully)和他的肺腑之言。他自己坚信一个定律,以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的方式赋予建筑物人类行为的属性,保持了西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和那个化名弗农·李(Vernon Lee)的特殊的移情理论。当我到纽黑文(New Haven)时,斯卡利已经注意到了希腊,并且神秘地将古代宙斯、赫拉和雅典娜的景观人性化,这后来变成了他失控的宣言《大地、庙宇、和众神》(耶鲁大学出版社,1962年)。
在一个好日子听斯卡利讲课,阅读他关于赖特、康或者奥林匹亚的文章,我发现了关于我们学科的两件事,或者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像其他历史一样,建筑史是一种人造品;有着事先想好的形式和一个精心雕琢的结尾;它并不存在于某种等待被揭示的原始状态中,并且是一种复兴的活力。无法用一个讲座或一本书来直接移植过去的体验——无论是现在身临其境的体验,还是过去使用者的体验。
然而,那正是建筑史家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在各种复杂研究和考证背后,重塑和表达实际的设计、建造过程,以及利用过去的人造景观。词句和图像是我们能用来完成这一基本任务的所有能用的手段:我们的词语,和我们能知道的他们的词语;现状图像和如果当时制作了并保存下来的历史图像。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有限的工具,因为我们所说大多是没有被证明的,我们的权威性在于信念和唇舌的技巧。
三、我作为建筑史家的第一个主要机会
我作为建筑史家的第一个主要机会与拉万那(Ravenna)的一座不大的砖石建筑有关,它离意大利海滨的里米尼(Rimini)游乐海滩不远。那是一幢不起眼的八角形瓦顶建筑,它就坐落在城中心大教堂旁边一个安静角落里的朴素花园中。当然,这不是一座普普通通的砖房子,而是一幢值得书写专著的纪念碑——一座洗礼堂。不用说别的,它已经历了一千五百个春秋。然后,当你经过一扇看起来不起眼的小门,会看到满墙令人眼花缭乱的金底马赛克图案和室内中央灰塑笼罩的大理石洗礼池。虽然门前由一名面容庄重、一身皂装的老妇人守卫,但这完全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令人惊叹的世界。人们在老妇人那里购买门票以后鱼贯而入室内,站在那里低声耳语,阅读他们手里小小的旅游指南,仰头并转动着身体观看那些在金色背景中灰塑的先知和头戴王冠的使徒,还有在约旦河中仅戴遮羞布的基督,古代河神从水中浮出,为这个新的上帝的化身献上一袭绿装。
我在这座小建筑中上上下下考察了几个月,观察、记录、测量。当下午5点钟关门时,玛丽亚请最后一位手拿攻略的游客离开后,就把我锁在里面,作为一种对我的优待。我会独自站在那先知和使徒的下面,试着想象自己如果回到5世纪中叶这个罗马晚期的首都会是什么情形,作为一个接受了几个月宗教训练的准基督徒,在那里我将会一次性永远抛弃魔鬼撒旦以获永生。
这肯定不过是一种猜想——谁又能真的知道呢?——但这好像对我思考那个想象中的古人很重要,因此我允许自己在《拉万那洗礼堂》一书里加入了一些关于他的段落。除此之外,这本书可以说在专业态度上没有瑕疵,有着一本严肃学术著作应该有的分析和那些世界上只有大概6名专家能够评判的神秘记述,大概也只有这几名专家会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这本书有着所有正确的元素——应有的风格和图像志,在时代精神的神坛上献上了一束鲜花,使那小小的纪念性建筑成为从古代晚期到后来兴起的拜占庭风格之间的重要转折点。然而我感觉到,使这个小洗礼堂这样的精彩建筑作品与宏大的理论框架相吻合,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于是,我在书的最后写道:“关于拉万那洗礼堂的陈述,就如同一切艺术作品一样,永远首先是个人的,其次才是历史的。”
另一个亵渎神明的念头使我偏离学者的正路。我看到玛丽亚在早晨开始一天的守护工作时总要在面前画十字。对她来说,这不仅是一座历史纪念碑,而且是她的主永久居住的圣地。这又是她工作的地方。在庇护着这座洗礼堂的小公园旁边,是她的住所,下班后在此存放着参观者登记簿和门票收入,其中一部分是她的工资。
这些简单的事实促使我思考。我现在确信,建筑历史有两面——那就是关于建筑环境传承的记录和我们对建筑环境的评述解释。我并不确定我其实已经开始思索“环境”而不是单体建筑;但是,面对大教堂、主教宫和玛丽亚的小住所,我可能确是踏到了建立一个文脉建筑史的边缘。这以后我明白了两件事:尊重地域的空间完整性——这就是说,任何一座建筑必须适合先于它存在的建筑群体的特殊布局;而且要尊重发展过程的先后顺序——每座建筑遵循一种随时间而逐步发展的形态。
但这还是在更多地关注建筑的客观存在。而人们居住在我们学科视为纪念碑的地域中,并且现在仍然住在里面;他们在其中娱乐、祈祷、死亡——循环往复。因此,建筑的历史也是,或者可以是,关于人类生活和生活场景的延续。为什么要打断这个故事?为什么建筑史家总是把建筑当作一些空壳子来写?
四、我的下一个研究课题
带着这些想法,我选择了我的下一个研究课题,加大了我研究的尺度。我选择了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地区,这个在开塞利市(Kayseri)附近的地区很引人注目——干旱荒凉,有着一种非常奇特的岩石地貌,满是皱褶和尖锥。在中世纪,希腊修道士在岩石皱褶中凿出教堂和居室,并画满了宗教壁画。这次我让自己往前走了一点。我形容了那有些令人生畏的环境和安纳托利亚过境通道的历史。我说起了那些修道士的生活和他们在土耳其征服者统治下的命运。我讲起了故事。
实际上比这更多。我完全知道,我写这本关于拜占庭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修道院环境的书,是在为我的专业研究寻求某种个人的锚点:我试图把我的著作和生活结合起来。要知道我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希腊裔家庭。那些修道院的所在地是我的家园,那些修道士与我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事实上,这个课题的选择只是一种巧合:写这本书是由出版社提议开始的。我知道我的建筑史不会都是自传式的。但重要的是选择把建筑历史看成对建筑物和人的解说,通过显示把我们和历史建筑联系在一起的是生活,从而有机会获得那六个专家以外的更多读者。生活从简单一般的建筑中涌出,这同纪念性建筑一样。区分“建筑”和“构筑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现在将毫无顾忌地承认所有这一切都太简单,太不真诚。许多建筑史家对本学科领域的偏狭和方法客观性的坚信引以为荣,与其相反,我们一直为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所动,这些事情往往是不明显的或者说得清的。孤立主义,在任何学科领域——如果真的存在——都将导致学科的极度贫乏。《神窟》(Caves of God)发表于1972年,那个时候我已经来到了伯克利。动乱的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影响了我们如何看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应该影响了我们。请允许我,从我个人的角度,随便地评说某些影响了我专业思维的人和事,我一直在为此自省。
五、动乱年代
我必须说到这动乱年代,因为这与建筑环境有关。我必须说到人民公园和波士顿市府大楼,说到城市更新和贵族化,说到对现代主义的挑战,说到莱昂·克里尔(Leon Krier)和罗伯特·文丘里。从那些事件到现在令人困惑但充满激情的辩论,我寻求建筑史家清白的终结——马斯和沃特金以温和的口吻大胆质疑的精英主义的,固执己见的,从根本上超然事外的,研究的长长记录的终结。而世界告诉我们更多,更多。建筑不是艺术收藏。建筑很重要——所有的建筑物,不只是纪念性的。它们是政治的工具;它们是我们作为群体存在的舞台;它们是带来社会变革和压制社会躁动强有力的手段。
我们可以从毁灭——战争的毁灭——开始谈起,战后年代胜利的现代主义使毁灭习以为常,臭名昭著的城市更新信条使美国城市中心地带变为废墟,就像是在找补我们在战争中幸免的炸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更爆炸性的话题可能是公民权利和尼克松,还有“燃烧——宝贝——燃烧”以及在越南的不堪入目的屠杀,但在这一切的中间是建筑环境。
我记得美国全国性的斗争和本地区的冲突。我记得麻省理工学院全班学生在因柬埔寨而闻名的1970年对波士顿市府大楼的愤怒——那是一座铭刻着地方政府腐败的、装腔作势的纪念碑,他们告诉我们这些听得进去的人,那些人多得惊人的花费本可以用来向城市贫民提供食品。我记得为了离我在伯克利教书的讲堂不远的一块空地而进行的恶斗,学校要把那块地用来修建宿舍而“街民”们则宣称那是一片开放空间。我记得那催泪弹、国民卫队,还有子弹。在美国另一端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要求确保有哈莱姆区到河滨公园和大学新体育馆的通道和使用权的静坐示威和由此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在巴黎,由巴黎美术学院建筑系学生发起的有名的1968年“五月风暴”,象征着把建筑美化为艺术的历史性终结,要求设计成为对改善社会的帮助,帮助人民建立他们的地域。在柏林,棚户居民组织起来结束了那里的美国式城市更新,这种更新就是铲除现有可用房屋,建造高价的高层住宅和高速公路。
在美国,60年代的革命使得对城市更新运动的矫正得以开始。1966年的美国历史保护法案中包括了一段我们认为很不平常的段落:
“国会发现并宣布……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应该被作为我们社区正在继续和发展的生活的一部分加以保护,以便使美国人们拥有一种方向感。”
新的国家历史名胜名录得到扩充,包括了有国家性和地区性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和地区。现在,纪念性建筑已经不足以代表作为群体的我们是谁,和我们曾经到过哪里。政府扭转了自己的方向。住宅和城市发展部开始设置社区发展基金来复兴历史居住区。内城见证了逐渐的恢复,那些一度衰败的地区又有了生机。
曾经兴高采烈同我们一起大搞城市更新的欧洲(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安东尼·萨特克利弗(Anthony Sutcliffe)1970年写的《巴黎中心的秋天》),现在又迫不及待地认可这种新的保护思维。1962年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热(Andre Malraux)提出了“特别保护区”的概念,并首先于1965年在巴黎的玛黑区(Le Marais)实施,然后不久又用于科尔马(Colmar)的皮革街,那里有木骨架建筑和石头铺砌的窄巷。
建筑史家脚下的地基在松动。行动主义者、建筑师、社会批评家都在强调普通的城市肌理的重要性,而这一直被史家蔑视而排除在他们关心的范围之外。有几本极具影响力的书使那些史家难堪。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爱德芒德·贝肯(Edmund Bacon)、1972年文丘里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1975年罗布·克里尔(Rob Krier)的《城市空间》使建筑史家连奔带跑地去发现中心主街,并且参与到城市类型研究中去。同时,快速传播的对现代主义前提的攻击从十人组(Team Ⅹ)的内部辩论开始,然后感到被先知们欺骗了的年轻一代加入其中,这迫使史家重新评价他们自己的过激——他们最信奉的先知们的观点,这些先知包括国际式建筑风格的主要辩护士亨利-罗素·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吉迪恩、佩夫斯纳。莱昂·克里尔坚信的论点是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促成了欧洲城市的形态分裂,并谎称国际式风格不过是一种风格,建筑史家的职责在于辨别形式而不必计较其后果,在每一个时期使用合适的风格并着眼未来而不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做的权威,对预言未来如何的智慧不用通过充分解释过去与现在而加以思考。
六、我的“第三罗马”展览
如果我在这里说起1973年我的“第三罗马”展览,那是因为在其中使用了混合方法,用来对付我刚才形容的建筑史学的悖论。我选择了一个在当时被认为不值得认真对待的课题。我们的权威史家已经断定那是时代精神的错误表达。另外,那也因与一个可耻的政权有关而有了污点。那时的评论机制是那样的不成熟,好像研究法西斯建筑就意味着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可。最关键的是,展览的主题显然是政治性的,涉及对记忆的设计。这使我们认识到,如亨利·米伦(Henry Millon)所揭示的,意大利史家在20世纪30年代与当时政权目的一致。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强拆政策的实质:用城市规划来重新建立社会结构。
要使人认识到这一切之中没有任何新东西,需要些时间:建筑从来都有着政治意图。197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由琳达·诺克琳(Linda Nochlin)和亨利·米伦主持召开了题为“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和建筑”的学术会议,会议论文包括关于建筑的几篇:理查德·斯台普尔福特(Richard Stapleford)的《康斯坦丁时期政治与中庭教堂》,将基督教早期中庭空间作为一种帝国与教堂建筑自觉嫁接的产物进行讨论;斯坦尼斯劳斯·凡·穆斯(Stanislaus von Moos)的《作为堡垒的宫殿:教皇朱利叶思时期的罗马和波隆尼亚》,是一篇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象征主义的文章;海伦·希尔英(Helen Searing)的《红旗飘飘:1915—1923年阿姆斯特丹住宅建筑》记录了左翼工会的建造活动;还有我的《皇帝和元首》,分析了法西斯政权的罗马奥古斯都广场兴建计划。我们这些与会者觉得从政治看艺术和建造具有前瞻性,但实际上相当陈旧。凡·穆斯指出:
“……建筑形式在建筑物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功能中仅仅具有次要作用。因此,一部直接的社会政治建筑史必须着眼于自身建造过程、它对社会劳动组织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统治权力为保证经济与政治稳定而对生产系统采取的操纵与组织的方式。”
在美国这只是开始——并且建筑史家在这方面不是做得最好的。《自觉和城市体验: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作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正在变得很有影响。(用这本书中他写的关于豪斯曼(Haussmann)改建的巴黎的文章与我们在以前所写的相比,就能看到主流建筑史家一直以来有多么幼稚。)在我们的学科中一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言谈,但很少有实际的应用。马里奥·马尼埃里-伊利亚(Mario Manieri-Elia)关于城市美化的文章与主流建筑史对这个论题的说法没有多大不同。《激进历史评论》杂志不时还发表我们学科的文章,说明唯一赎回我们以前清白的方法是像其他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的领域那样使建筑学科政治化。像麦克尔·华莱士(Michael Wallace)关于威廉斯堡这样的文章已经证明了这样写的历史将会怎样不同以往,那篇文章说明威廉斯堡一直是灌输美国右翼意识形态的舞台。
七、其他相关学科
我们话题的第一个方面是实际生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把环境推向了社会争斗的前台,这迫使建筑历史重新考虑其传统责任。这引出了我要立论的第二个方面。这肯定与其他相关学科有关,这些学科发现建筑环境是值得他们研究的课题,并且在建筑史家——我想要说“不敢涉足之处”,但更确切地说是——“没想到的地方”,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工作。
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不知从哪里开始。但肯定至少涉及历史本身、地理学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涉及的任何学科。
我不能想象任何建筑史家在读福柯的《古典时期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或者《规训与惩罚》时不会对我们建筑史家在建筑研究中使建筑变得微不足道并乐此不疲而感到尴尬。这些巨著证明权力和公正如何与像医院或监狱一类的机构建筑紧密相连。福柯关于“作为一种定义人类日常生活权力关系的手段的”圆形监狱的讨论应该使我们自己相当不舒服地和我们四平八稳的形式主义解释相比较,我们将其说成是理想城市的一种图示,一种新古典主义的设计,并把它和其他中心布局的设计放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在大集市的小摊子上比较纽扣一样。我在想,对福柯那样具有穿透性思想的头脑,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最多能把圆形监狱说成是“一个结构……从风格主义的理想城市推延出来的……一个住宅本身就是一个小城市,一个阿尔伯蒂预示过的概念。”对于“管教建筑”和“坦白建筑”这样的类型,我们有任何用处吗?我们会看到像福柯那样把建筑定义为“一种支撑性元素,确保某种人在空间的分布,人流的划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程序化” 的紧迫性吗?
由于福柯,我们也许会不无益处地记住普遍性的无用、那些我们前辈用来决定所有时代形式问题的令人麻木的庞大体系、循环往复发展的认知方式,或时代精神的不可避免性。也许,已经到了我们也应该同意“没有外在确定性,没有在历史与社会以外的普遍性理解”的时候?
对于历史学科领域本身,假如我们建筑史家没有一直把自己的教育看成独一无二,我们不知道已经学到多少东西。历史学科最优秀的学者没有等到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历史可以并且必须从底层往上写。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946年就发表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我们之中没有一位在那时想到我们学科如果也着眼于“长期持续”将会怎样——我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于阅读我们学科之外的东西,也因为我们的时间大都用在反复分辨、遴选历史长河中几个屈指可数的事件和与其相关的几百座建筑,而人类每10年就在其创造的古老模式中加建成千上万的房屋。当《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在20年后面世,我们还是看不到对世俗课题的学术关注能教给我们什么,这些课题包括服饰、饮食习俗、货币和日常必需的面包。现在,我仍然期盼建筑环境的历史能有与布罗代尔1979年改写版相当的标题:“伟大游牧民族的消失”“麦子和其他谷物”“大米的重要性”“布置餐桌”“中国家具的双重图案。”
布罗代尔在一个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家……应该注意把人类科学综合起来……而不是只追求自己领域的完美。” 然后又说:“我们这一行令我觉得奇妙的是其能解释在我们面前编织起来的人类生活的程度,和面对变革或传统时的默许与沉默,拒绝,同谋,或投降。”而我们只能说一声“阿门”。
一个与布罗代尔所说的认识平凡东西的重要性相平行的学科是文化地理学。在伯克利,约翰·布林克尔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就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大师。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比我从建筑历史的专著和分期通史中还要多,例如他的《美国空间》和收入《废墟的必要》《发现乡土》中的论文。他们给了我们乡土,他和他的直接继承者——如约翰·R·斯蒂尔格(John R. Stilgoe)——并非将乡土简单地甚至单一地看成美国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住宅建筑,而是认为它包括了农业和工业建筑、快餐摊子和加油站。并且他们的乡土概念包括更大范围的环境,从农庄(例如:1984年出版的托马斯·C·胡布卡(Thomas C. Hubka)的《大房子、小房子、后院、谷仓》)到整个景观。当所谓商业考古学家将拉斯维加斯大道和莱维敦这样的环境也看成乡土的时候,数十个细致有启发性的研究项目避开了这种轻松的反向势利,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中心主街和铁路通行权,还有汽车露营地和郡法院广场。
同时,英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工业考古学为濒危建筑物和环境系统的研究注入了活力——酒坊、水坝、桥梁、运河、辅助设施、矿区景观和员工居住区的住宅模式。大西洋彼岸的肯尼思·哈德森(Kenneth Hudson),布赖恩·布里斯格道尔(Brian Bracegirdle),还有巴瑞·特林德尔(Barrie Trinder)都是值得关注的学者。
与这些对乡村和郊区景观的研究(例如斯提勒哥的《大都会走廊》)相应,城市地理学者也在非常精确地研究城市。他们怎么可以把这本来属于我们的世袭领地夺走!哈罗德·卡特(Harold Carter)、康岺(Conzens)父子和其他几位学者,在城市肌理研究方向创造了奇迹——那并不是使我们感到满足的,像A·E·J·莫里斯(A. E. J. Morris)的《城市形态史》(1974年)中那种对城市肌理的研究,而是深入到用地分块和建筑物排列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我们终于应该知道我们不能只是通过关注街道规划来写城市形态史。“从功能和传承上”,如老康岺所说,“街道系统和相关的地块形态是相属的;它们不能被单独考虑。”
他们的研究对象现在包括构成城市的所有方面和元素——用地、交通系统、工作和居住的关系、城市边缘带、中心商业区。当我们仍然在基础层面理清有机的中世纪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如何实现视觉规范化的时候,是城市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在16世纪初当城市土地变成一种收入的来源时,一场重要的变革发生了。詹姆斯·万斯(James Vance)坚持认为土地拥有权在中世纪城市中主要是功能性的——人们用来谋生、种菜、养牲畜、制造并销售产品。人们以一种托管的方式持有一块地,以便成为有用的公民,而并非要增加财富。拥有土地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使人获得选举权,有资格参与城市事务,并在城市结构中获得一个指定的位置。后来用地和拥有权发生了分离;土地的价值因而变成由租金多少而定,成了财富的来源。这个从土地到租金的渐变“结束了有序城市的理念并且在经济上鼓励了用地的隔离”。这种水平的辨别才是城市形态研究所应该追求的。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尽可能吸收这些内容。我写了一本教科书,在那本书里我只做到了一半。这是因为,我开始写作是在1973年,要我从在耶鲁学到的东西中解放出来还为时过早。在写那本书的10年时间里,虽然我变得越来越大胆,但还是不够。
至少我认识到,一定要努力把建筑理解为所有建筑物,无论在何时何处。我们学科的名字—“建筑历史”,要求我们抓住什么是建筑。对我来说,我希望我那本书的读者或者在课程中使用那本书的教师明白,现在一定要将建筑理解为所有建筑物——既包括一般的,也包括花哨的——以及它们在形式的景观中的所在。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我要讲一个故事——人类占有土地并通过建造行为形成社区的史诗般的故事。” 我把它叫作《一部建筑史》以明确表示:有多少建筑史家就可以有多少部这样的建筑史。
八、投入决定我们未来环境的斗争
我坚持认为,只从建筑本身解读文化不是一种好的方法。你必须自己博览群书才能读懂建筑物。而且没有确定的解读。
“仅限于当我们能够接收到它的信息时(我曾经写道),建筑才是一种文化表达的媒介。并且这些信息是通过我们当下思虑的问题发掘出来的。我们通过建筑对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区文化的解读可能会使我们对自己有同样多的解读。”
归根结底,建筑史是一种今天的我们和我们所探索的某时某地的私密对话,而史家是对话的主持人或调解人。
我在书中把故事一直讲到今天。这对我有很重要的象征性。在学校的训练中,与当今保持一定距离被认为是历史家一种好的作风和举止,这就是说,要等暴风雨过去后才能解释它为什么来临。而我不再想保持这种作风和举止。我现在坚信我们史家必须带着我们自己的特殊天赋,投入决定我们未来环境的斗争。
由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建筑史研究必须在几个层面上展开。首先,课题本身就很关键。它是一个文科课程中的重要学术主题。
但建筑史又有着更实际的关注——并且这是为了行业和大众。建筑史是一个为建筑行业服务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历史家一直对在工作中涉及这一点而感到不安。但对我们经常被问到的“历史对建筑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另一个问题:“哪种历史?” 对建筑的制造者来说,历史是一个采石场,特别是我们目前正处在的这个时期——随着否定历史的现代主义的收敛期而来的肯定历史的时期。在形式上受欧斯提亚(Ostia)或其他欧洲古城的启发没有什么不对,但建筑师自己就是这种形式关系的专家。通过观看图片和实地旅行,他们可以吸收一个罗马风建筑立面、一个雨淋板风格住宅、一条有特色的街道和公共空间所传达的信息。在这方面,他们不需要我们。当设计师开始把某种理由附会给他们所爱慕的形式,而这种理由对历史不负责任或者随意歪曲时,这种对过去时代的挖掘就变得不可接受了。这时史家就必须介入了。
不管史家是否愿意承认,“历史主义”的回归给了他们新的任务。在建筑学院执教的我们,必须估量当下对我们的期待。如果我们要按其需要帮助后现代主义,我们不应该比建筑师自己在呈现过去的视觉记录方面做得更好吗?如果我们对这种新的回归所代表的肤浅的复兴主义感到惋惜,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完全展现它所能涵盖的全部建筑历史,以便说明把建筑看成一种艺术并且只用审美作为评判的标准不再可行?——假如这一标准在过去任何时候曾经真的行得通过。
但是我们学科有一种更广泛的合法性。作为拥有集体记忆的人群,我们都应该知道如何解释构建领域的林林总总。作为建筑的消费者,我们应该直接参与和了解我们周围都设计和建造了什么。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处在某个经过设计的环境中。我们在建筑中生,在建筑中死;我们把书籍存在建筑中,把罪犯关在建筑中,在建筑中照顾病人,在建筑中立法,在建筑中制造汽车。所以人们对建筑这个主题关注的普遍程度应该理所当然地不亚于政治、饮食、和性。我们越是对作为共享遗产的建筑有兴趣,我们就越坚信它的存在和演化对我们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就越应该懂得建筑历史。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为什么大众对建筑基本上漠不关心呢?建筑史家和建筑评论家肯定做了什么而使得这种淡漠得以强化。首先,建筑很吓人,因为在技术上很复杂。人们不容易看懂蓝图、飞扶壁和轴测图。再者,建筑学被吹捧成一种大师艺术,并且对艺术的评判不可避免地要设置成催生异化的从专家到外行的等级制。我们越是把建筑当成宝贵的、有谱系的艺术品,我们就越是把它们拔高到一种高级时尚——稀有并且最终变化无常——的境界。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大众以建筑为荣。
(1)作为艺术,优秀建筑物给人们欢喜和享受。但问题在于质量评判的完全任意性。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在1914年说过:“我们依赖于一些对建筑评判的习惯,这包括对破碎的传统的依赖,随意和偏见,以及在这之上的那些大道理,它们或多或少似是而非,半真半假,不着边际,没有经过批评论证,并且往往自相矛盾。按照这样的评判,没有一座建筑物可以被认为糟糕到毫无合理之处,或者好到无懈可击。”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适用。海尔姆特·雅恩(Helmut Jahn)设计的费城自由广场1号被保罗·戈德贝格(Paul Goldberger)赞扬为杰作,以及自20世纪30年代传奇的费城储蓄基金会大厦以来最好的高层建筑;但同时又被马丁·菲勒(Martin Filler)谴责为对天际线的可耻虐待。这种随意性不仅导致了评论家之间存在争议和似是而非的分歧,还产生了一种令人窘迫的公众趣味与专业趣味的离异。
我们将对建筑的评判局限于审美,从而忽视了建筑的社会效果、政治作用、功能问题、伦理道德。 波士顿科普利广场的约翰·汉考克大厦是一个漂亮非凡的艺术品,但它尽到建筑的社会责任了吗? 我们是否应该为其给城市带来的抽象的美而鼓掌? 或是为其不道德的放肆,和对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基本平衡的长期影响而加以谴责?
(2)建筑被珍视也是因为它能提供集体认同的形象——让人们引以为荣的形象。参观和观赏哥特式大教堂非常精彩。它们也是一种象征,使法国人、基督徒或西方人引以为荣。但是建筑史家同样是在玩一种头脑简单的游戏——把注意力聚焦在纪念性建筑并将其视为我们的文化认同。然而,那些建筑纪念碑总是代表我们自己引以为荣的公共机构吗?例如,难道我们应该到赫斯特城堡或者私有化了的城市商业中心区去寻求我们的集体荣誉?单单用纪念碑足够代表我们吗?平常的城市肌理和乡村就没有意义吗?当我们说锡耶纳(Siena),或孔克(Conques),或楠塔基特(Nantucket)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正如我曾在别处说过的“每一个建筑物都有故事可讲…… 在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里,生长着一个不断积累的社会图画和这个社会养育的价值观。”
我目前的信念,也是我近期研究工作的动力,就是建筑历史所扮演的角色比我们能允许自己相信的更为重要,更无所不包。我们需要使建筑变得平易近人,使其进入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使其在高尚的同时变得世俗化。我们需要坚持在建筑评判中包括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也就是实际上的公民要素。我们需要对我们周围的每个人表达这样做的迫切性。作为一个好公民,我们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我们的建筑环境的形态、发展的节奏、计划或正在实施的改变施加影响。文化和建造领域是相互依存的。建筑历史的限度一定是与我们文明的水平相当的。
译者按:
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是20世纪后期美国建筑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他于1936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希腊裔家庭,大学毕业以后在美国耶鲁大学读研,兴趣从戏剧转到建筑历史,在艺术史系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四年之后,他离开耶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任教,教授建筑历史课程,直至1991年55岁时英年早逝。科斯托夫著述颇丰,出版了多部建筑历史专著,并编著了美国建筑院校广为采用的建筑通史教材《一部建筑史:场所和礼仪》 。科斯托夫是一位富有革命精神的建筑史家,勇于质疑、挑战、突破陈腐的建筑历史学科传统,提倡跨学科的借鉴,致力于创立一种包容建筑所在空间和社会政治生活文脉的建筑历史。他所提倡的建筑史不再限于过去建筑形式的风格迭代,而是人们为改善未来生活环境而争辩的论坛。这也反映了他充满对社会人文关怀的个性和作为公民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
作为讲演稿,原稿的段落划分比一般学术论文短且无标题。译文保持了原稿段落划分的方式,但为方便读者尽快掌握全篇结构,译者对译文进行了划分并用原文中的言语作为每一部分的标题。对于读者熟悉度不高的人名地名,在译名后面加入了括号中的外文原文,以方便读者。由于作者对原文的尾注采用了简便省略的格式,译者增加了括号中的补充信息。另外翻译过程中还补注了作者未加注明的文献信息以便读者查询参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赖德霖教授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本文节选自“文化与人造世界——建筑史的限度”,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8月刊,总第200期P122-130,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200丨2019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