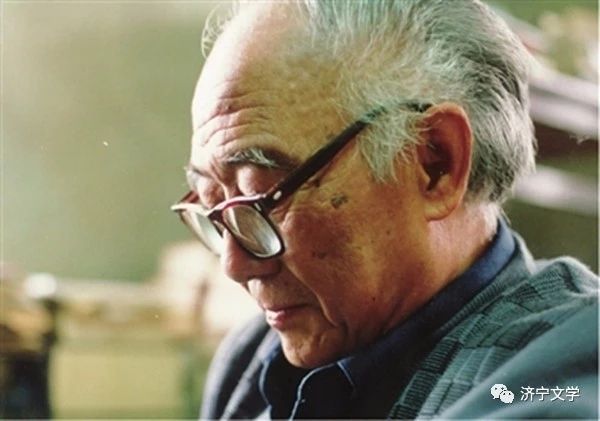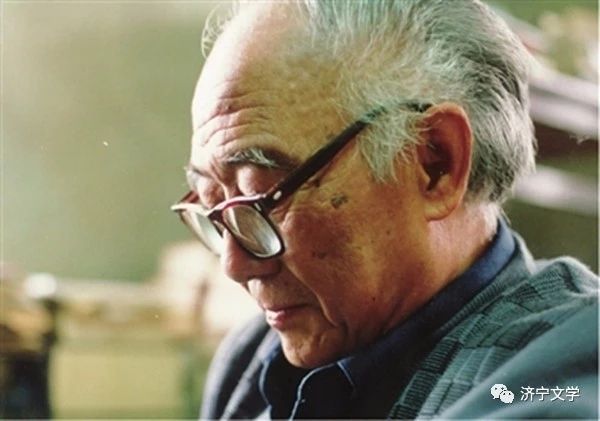
中国文坛还算是幸运的,二十世纪末叶出了个作家汪曾祺。一个随和的老头,不经意间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谁知这不算丰硕的文字,竟然天雨般隐于云彩里,时不时就淋湿了天下人(尤其是普通人)干涸的心。他甚至不能归类于“作家”这个群体,他的写法与写作心态都呈现出一种“异类”的味道,把写作当作敲门砖、以敲开各种利益之门这种等而下之的做法自不必说了,就连呕心沥血图个传诸后世的“高境界”,他也没有。好似一泓水,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了,浇着了菜菜青了,灌着了树树绿了,或者浸活了种子长出了庄稼,甚至什么都没润泽只自个儿活泼出一曲天籁,都顺其自然。
但是这泓水又是人间的水,亮晶晶地染着人间的烟火。只是一个“善”字一个“美”字使他有了超常的法力,乾坤的枷锁束缚不住他,功利的诱惑更左右不了他。生时,他痴痴地恋着人间;死了,人间便常常地想着他。尽管也有误解,总是无法抹杀广大的普通人对他与他的作品的喜爱。比如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士大夫,有人说他淡泊得像天上的一块白云,其实都不大准确。
众说纷纭之中,胡河清与摩罗对他的探究可谓别具一格。胡河清先生在《灵地缅想》一书中说:“汪先生处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漩涡里,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敬慎不败,得力于道家的谦冲之道亦深矣,”并说汪老先生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境地中有三种躲避解脱的办法。一是躲入有着极强“间离效果”的京剧,“似醒非醒,冷眼觑着喧闹的尘世间不断上演着的一出出闹剧、悲剧和喜剧”;一是躲入美食之中,让口腹之欲“使思想活动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状态”;一是躲入青年男女的爱情之中,“编造关于巫山云雨的梦境成了他们对于残酷历史过程的一种特殊的心灵规避方式”。摩罗先生则在胡河清躲避解脱说的基础上,更分析出了汪曾祺不敢直面人生的“瞒”和“骗”的“温馨”,甚至把他视作“一个个性生命自我取消”的“悲剧”——“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
但是汪曾祺在历史的天宇中、尤其是在文学的银河中,到底是怎样一种星座呢?
我们还是先从他的内心剖白中探寻一下其灵魂的真迹吧。
他说:“一个随人俯仰、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那么他的个性是什么呢?从对他影响较深的中外作家归有光、鲁迅、沈从文、废名和契诃夫、阿左林是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的。他对于西班牙阿左林的评价是“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 (《谈风格》)。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个性恬淡,却因善良而对普通人敞着炭火一样的心怀;不事张扬,喜静守独,又因热爱而全身心地融入生活并对生活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他在《自选集重印后记》中直言:“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世事是悲哀的,便让悲哀渗透在作品里。普通人里又毕竟生长着美与善,那就在作品里“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他是那样地理解与欣赏老师沈从文,说他之所以写《边城》、《边城》之所以写得这样美,就是“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 (《又读(边城)》)。这不也是他的自况吗?“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小说三篇》)“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他是本质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对于非人道的东西,他虽然没有电闪雷鸣、金刚怒目式的抗争,却也绝对没有苟且躲避,取消生命的自我,更不会认同与合流。胡河清与摩罗虽然对汪曾祺作了独到的研究,但其结论却因进入他的灵魂而又从他的灵魂深处滑开,从而过犹不及,离开了真正的汪曾祺。
真正的汪曾祺有着自己的愤怒与抗争。
对于写过《骆驼样子》、《龙须沟》、《茶馆》等传世之作的作家老舍的投湖而死,他在《八月骄阳》一文的结尾,写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这么个人,我想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呀’!”“‘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这与《茶馆》里“我爱国可谁爱我啊”的那句台词,何其相似乃尔!这是轮回还是停滞?是前进还是倒退?是解放后的“新”还是唱了两千年终也唱不完甚至更加变本加厉的“老调”?数十年的光阴竟然白过了吗?只这轻轻几句对话,便向国人揭开了掩饰着悲剧的帷幕。
对于当年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被赶被骗被“流放”,汪曾祺更是进行了撕人心魄的控诉:“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癌肿。是什么人忽然心血来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纯洁、轻信、狂热的年轻学生(老三届)流放到‘广阔天地’里去的?这片天地广阔,但是贫穷,寒冷,饥饿。尤其可怕的是这片天地里有狼。发出那样号召的人难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层干部是怎么回事?把青年女学生交给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来往狼嘴里送。我们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笔债的”(《一个过时的小说家的笔记》)。将无罪的“整整一代”年轻学生进行“流放”,这不是一种深重的罪孽吗?而且这种罪孽还竟然是一种“心血来潮”式的随意试验!否定与愤怒的笔触,更直接指向那个“发出那样号召的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当过“右派”、而后又在“文革”中倍受凌辱的人。他之所以对于自己的苦难能够“随遇而安”、甚至感到“三生有幸”,也许是他的眼睛老盯着普通人的苦难、只顾怜悯而忘记了自己的缘故吧?但也正因为自己有过长时期的切肤之痛,也才能直针穴位,一语中的。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发着悲愤的喟叹,直言“‘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呼吁作家“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 (《文集自序》);“还是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我担心画眉忙着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录音压鸟》)
北京国子监的那通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碑,一定在他心头压了好久了。碑上,明太祖将惩治闹学潮学生的办法定得明明白白:“凌迟了,枭首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将人零刀子片了,再割下头挂在杆子上示众,而后还要株连九族,流放全家。汪曾祺对此一点也没客气,说“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国子监》)。这就是封建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一种将鹦鹉学舌定为主旋律的不许自由发声的政策。从明太祖朱元璋到北洋军阀段祺瑞,再到国民政府蒋介石,五六百年间,只从凌迟“进步”到枪杀,真可谓换汤不换药,不许自由发声的独裁与专制依然不变。
经过了“反右”和“文革”的汪曾祺,回首间早已走出自己构筑的“随遇而安”的小巢,发出了自己心底恸然的鸣唱:“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随遇而安》)
看到被普通人摸得鼻子发亮的美国总统林肯的铜像,这个儒味十足、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人,一定是对孔夫子的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怀着深深的厌恶吧?此时此刻,他不仅想起了林肯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那句名言,而且感慨系之:“自由是要以平等为前提的,中国很缺乏平等。”“国内搞了那么多运动,把人跟人之间都搞得非常冷漠了。回国之后,我又会缩到硬壳里去了”(《美国家书》)。这些家书,是他在1987于美国讲学时写给妻子的。其时,国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又过了将近四年,这个随和的老头,再一次地实话实说:“我们这个社会迄今仍带有很大的封建性,甚至奴隶社会的痕迹。”(《一种小说》)
但是,汪曾祺毕竟是一位“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不擅愤怒,长于慰藉;不擅谴责与鞭挞,长于赞美与咏叹。他要用对于脆的人心的体贴与呵护,对于人性的呼唤与热爱,和对于隐于民间、渗透在生活中的善与美的发现、再现与礼赞,完成他的世纪末的绝唱。
巨大的爱已经让他进入到忘我的境界。他只顾勤恳地疏松着已经板结的心田,默默地播下富含营养的种子,坚信再多的灾难,也不能永远夺走人类丰收的季节。我看到,一尊洋溢着人性的善与美的女神,正披着晨曦,仪态万方地塑起在东方。
在汪曾祺的著作里,很少提到鲁迅。鲁迅和汪曾祺是两种性格的人,一峻急,峻急如暴风中的大海;一舒缓,舒缓似春月下的小溪。但是他们又有着相通与相似,这便是在他们的心之深处都有着茂密的爱,而且是母爱。汪曾祺特别记得并着重提起过萧红与鲁迅的一次对话。萧红有一次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思索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对此,一贯浓情淡出的汪曾祺似乎也掩不住情感的波澜,说:“鲁迅的话很让我感动。”接着,又带点悲凉意味地补充道:“我们现在没有鲁迅。”这些话,他说在1991年的1月。
而他的“我们现在没有鲁迅”这句话,正是他以母爱之心,为青年黑孩的散文集所写序言里的一句话。就在这篇序言的最后,他还像母亲一样祝福就要远去日本的黑孩“一路平安”。从他喜欢、理解、体贴、尊重、学习青年的言行里,我感到已经久违的鲁迅式的母爱。他为何立伟的小说集写序,七十多岁的人,整整花了两天的工夫,写下了四千五百多字。只在末了点出立伟初期作品“奇句过多”的毛病,还怕伤了青年的创作热情,疼爱地自语着:“不知道立伟会不会难过。”(《从哀愁到沉郁》)
实际上,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往往就是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尤其在情感被规定、规范成一条河流,必须注入带点神癨味儿的庞然大物的时候,这种爱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所以汪曾祺在敏感却又最易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身上,在生计艰辛却又少有依靠的普通人身上,付出着,也发现着这种弥足珍贵的情感。当然,他的生命,也便在这付出与发现的同时,获得自慰与欢悦。
他被明代散曲大家王磐所感动,就因为王磐通过“目验、亲尝、自题、手绘”,为没谁真正关心的老百姓编了一部《野菜谱》。他为也同是明代的诗人、状元杨慎的悲惨命运而泪下,并缕述其因“言论自由罪”、只身被贬谪云南三十七年,直至七十一岁上孤单地死去的痛苦一生。对于他的老师沈从文,他更是用理解、用自己的做人和为文,表达着钦佩和热爱。他知道老师本来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他知道不能写作的老师心里积藏着沉沉的郁闷,知道了又不能说出,只好让理解与爱化入告别遗体时的泪水里:“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那以与普通人为伍为荣,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封建士大夫简直是和他南辕北辙,更遑论“最后一个”。
1986年,离家四十七年、已经六十六岁的汪曾祺回家了。回家的汪曾祺没有忘记自己上幼稚园时的王老师,去看她,带着北京的果脯,更带着专门为老师写的一幅字:“‘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师恩母爱”,在汪曾祺心中已成不涸的圣水。就是这首诗,让王老师哭了一个晚上,也为老师寂寞的晚年,平添了温馨的暖色。
他还会对因“偷人”而被丈夫用劈柴打得很重的卖烧饼的女人“充满了敬意”;那个背着扬琴、点着麻秆、踽踽而行的盲老人,又会令他“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吗?”难怪他要呼吁引进美国盲人的夜光麻秆,好让人在黑夜里为盲人让路;从小声说话、低头走路的画工管又萍,他体察到了从来不署名的画像画工的辛酸;至于发生于旧社会的、挑夫的女儿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的“自由恋爱”,冒死从潭中捞起女尸、却将挣来的十块钱全给了人治病的“陈泥鳅”,他更是给以倾心的赞颂。
别说人了,就是动物草木,也能牵动起他的情感。1980年12月29日清晨,他写了《天鹅之死》,对那位伤残于“文革”工宣队的凌辱之下的芭蕾舞演员白蕤,对那只毙命于“文革”之后青年的枪口之下的白天鹅,倾注了全副的热爱,并用流血的心呼唤着人性的回归:“天鹅天鹅你在哪儿?天鹅天鹅你快回来!”以至七年之后,当他重校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是“泪不能禁”。
就这样,在冷酷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他捡拾起被人遗忘或被专制统治者践踏的仁爱、善良的人性种子,拂去蒙尘,育出一株株小苗,再用心血勤勤浇灌。他知道还会有风有雨,甚至风暴冰雹,但是他坚信,这些小苗,肯定能够长成大树的。只有具备了这种树木生长的环境,只有这种树木连成海洋般的森林,人间才有味道,中国才有希望。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坦言:“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尊重和欣赏。”(《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心里头有神不?有。他全身心地敬这个神、爱这个神。这个神不是天上玉皇、海中龙王,而是上面说的那位人性女神。这人性之神,善是当然的了,还有一面那就是美。面对龌龊和险恶,面对无助和绝望,面对苦难与死亡,汪曾祺总是乐此不疲地告诉人们:瞧瞧她,瞧瞧她吧,瞧瞧这位美的女神,她就在你的身边,她就在我们的心里。
“飞起来露出桃红色的翅膜,格格格地响”的,是绿蚱蜢;“不紧不慢,汤汤洄洄,似若有所依恋”的,是伊犁河;“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是老舍;“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的,是一对童心未泯的摘枸杞的老人;而为丈夫前妇的小男孩儿买下好多东西,又用勾针给其勾一顶大红毛线帽子、有着“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的,一定是那个爱上个放蜂人的四川女人了。
人性的恢复,我们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我们欠账太多。不要说去发现、欣赏人性之美,我们甚至还在以人性之丑之恶为美,而把真正人性之美的花蕾踩入烂泥中,或扼杀在心灵的萌发时。我们总是强调整体而忽略了细胞,甚至不惜窒息、扭曲一个个细胞的活泼的生命,来换取整体暂时的平衡和稳定。其实,整体的健康与活力,全仗着细胞的健康与活力,一旦细胞出现了无可逆转的癌变,等待着整个肌体的,只能是完结。汪曾祺先生自从将美育的担子挑在肩上,就再也没有松闲过。他说“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认为美育“是医治民族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关于〈受戒〉》)。
所以,他将美推向了极致。
《葡萄月令》里葡萄简直就成了仙子,读来让人心头美得酥酥地离开了一切凡尘——“一月,下大雪……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窑里。二月里刮春风……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枝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三月,葡萄上架……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八月,葡萄‘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得像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串,饱满、磁实、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是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所以,他把情推上了极致。《受戒》当是不朽的传世经典。
美丽的村姑英子与聪慧的小和尚明子的纯真爱情,在美丽的湖中涨向高潮:“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1997年,七十七岁的汪曾祺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走得这样早。看相的说他能活九十岁,他虽然不敢想得这样长,却也绝对要比七十七岁久长。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他还打算再写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聊斋新义》,还有一部已经酝酿成熟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这个达观随和的老头,其实是有点怕死的,他说:“活着多好呀!”
只是他已无法知道,很多的青年、很多的读者都会时不时想起他,并在心里念叨着:“要是汪曾祺活着多好呀!”其实,活多大是大?关键是质量。有他这两百多万字的作品在,他就会活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尤其在人性珍稀奇缺的时候,大家更是忘不了他。他说过:“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我们当然还会记得,他说过:“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一两千年之后,当人性已经得到足够的提升,人们也许才会渐渐把他淡忘的。谁知道呢?说不定人们回眸间倒会把汪曾祺看作英雄呢——没有勇气、力量、智慧和献身精神,谁能够像他一样在黑夜里举起照亮而且温暖着人心的火把呢?
汪曾祺走了,我们还在。
作者简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高级编辑。1952年生于山东济宁农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出版诗集《翠谷》、传记《布衣孔子》、散文集《乔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阳光》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散文《微山湖上静悄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获中国散文协会冰心散文奖,作品入选全国各种选刊、选本、大中小学读本及初、高中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