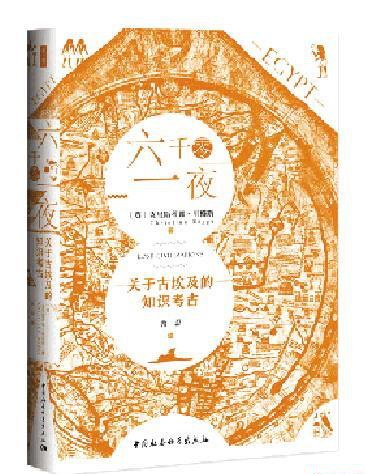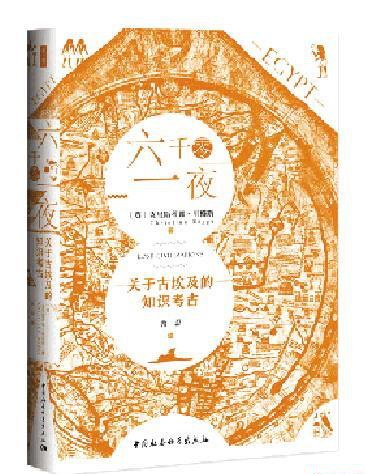
□ 林颐
一部埃及学著作,为什么要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讲起呢?似乎有点奇特。
据作者克里斯蒂娜·里格斯的描述,弗洛伊德终其一生都是狂热的业余考古学家,他的心理咨询室堆满了来自古希腊、罗马和埃及的雕塑等各类古董。另外,更重要的是,《六千零一夜》这部“关于古埃及的知识考古”的作品,可以借用弗洛伊德“记忆遗失”的观点作为理论的依据,这是全书的一个出发点。
记忆史是贯穿20世纪的文化史,有时也被称为“文化记忆”或“社会记忆”。对这一主题的学术兴趣发源于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七卷本《记忆之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谈论记忆,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了”,诺拉的这句话印证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逻辑:即一个现象要先消失,才能完全进入人们的意识。意识大致上是在“过期的标志下”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本书要从弗洛伊德谈起,我们需要像解读个人意识那样去解读社会心理,去打开尘封的记忆。对于古埃及这类失落的文明,尤其适用。
从弗洛伊德切入,也提示了我们,《六千零一夜》不是历史论著,本书牵系“六千零一夜”的悠久历史,但作者不囿于历史,不做线性的叙述,而是更关注古埃及文明在现代世界的投影,或者更确切地说,作者关心的是现代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以及用什么方式建构了古埃及的形象,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秉持的是当代文艺批评的立场。
巴里·肯普在《古代埃及:对一种文明的剖析》里说过:“我们可以走入和走出“古埃及人”的思想世界,而不觉得他们的思维怪异,因为他们的语言和图像也是我们西方人自出生以来用以给现实世界分类的一种方式……我心中的古埃及更像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尽管我希望它不会与原始古代文献有太过明显的出入。”尽管古埃及已经“死”了,可是,有些亘古不变的东西与怀旧的力量总能使它死而复生,让它魅力永存。
最早把埃及人作为独特而有趣的人类学考察对象的是古希腊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希罗多德的《历史》等都有大量描述,前47年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毁,有关埃及的文献存世很多,在《圣经》里,“摩西出埃及”是有名的场景。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学”,而只是欧洲的古物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埃及学,要到19世纪上半叶才形成。
作为东方文化的爱好者,拿破仑的兴趣带动了一系列主要针对埃及和近东的殖民扩张,并产生包括商博良解码楔形文字在内的一系列辉煌的考古学成就。在这个过程里,法国有一个对手,就是英国,英国对埃及的兴趣向来也浓厚。本书作者克里斯蒂娜·里格斯就是专职从事古埃及考古研究的历史学家,在18~19世纪,英、法两国就有很多埃及学家。当时这些学者的工作,实际上要放置在英、法两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激烈竞争里。所以,本书会提到萨义德与东方学,我们要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里去理解欧洲人对古埃及的兴趣。
萨义德指出,自18世纪末以来,东方主义,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是“西方风格的统治、重构,以及对东方的主宰”。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有关埃及的书写,那些西方的旅行者、小说家和学者在认知近东时所使用的各种图示,比如宿命、奢侈、落后、消极、耽于声色等,难免就戴上了有色眼镜,或无形中带有恩赐或居高临下的态度。萨义德的学说未免偏激,不过的确指出了西方的偏见给埃及学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现代人对古埃及的想象有着强烈的浪漫化倾向。作者谈到,在19世纪晚期,西方的“埃及热”已经达到了痴狂水平,欧洲人的室内陈设、服装款式和建筑风格都被“埃及风”裹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曾经流行的“中国风”和“东瀛风”。与这两股风潮相似,埃及风最初的、最热烈的劲吹者,都是法国。法国人喜爱表象的华美、东方的奇异风情,但在本质上,这是一种群体意识的共谋,是被欧化的想象。直到如今,在有关埃及的文艺创作里,比如电影《木乃伊之夜》、奇幻小说《木乃伊的脚》等,都把设置的古埃及背景氛围弄得诡谲恐怖而又奢靡绮丽。大众非常喜爱这些作品,认为古埃及就是这样的。
谈到埃及人的民族身份,难以回避这样一个当代问题,即从种族和民族的角度来说,埃及人是否就应当认同为“黑色”人种。作者提及了一起公众事件,传媒巨头默多克在2014年11月看过好莱坞电影《出埃及记:法老与众神》之后发了一条推特,与其他观众就这部电影的全白人演员阵容展开论战。怎么看这类现象呢?作者说,默多克从自己的社交经验出发,认为,或者应该说乐于认为,现代埃及人都是与他一样的白种人。不过,从现存的木乃伊与古埃及人的描绘来看,考古学支持“黑色雅典娜”,埃及文明在本质上是“黑色”文明。如默多克这样的反对者,通常无视材料与证据,斥之为“非洲中心论”立场。对很多非洲人以及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说明非洲文明和黑人文明在世界早期文明里曾经起过源头的作用。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种族斗争与解放运动里,曾经有很多种族论者认为法老埃及是来自欧洲的“优等民族”建立的。
作者还批评了长期以来对于古埃及女性形象的歪曲。比如,作者以法国画家让·热罗姆作于1866年的油画《艳后初会恺撒》为例,说明那时的艺术家对裸体白人美女、东方妻妾、妓女与放纵的男欢女爱的心理幻想,克娄巴特拉七世就是在这样的思维里被固化为“埃及艳后”的角色,但很少有人去真正研究、理解埃及社会里以妇女为中心的那些方面。对民族、种族、性别以及性的讨论表明,在当代埃及学研究里,这些话题无疑是极具争议也是极其有吸引力的。《六千零一夜》立足当下,联系古今,这是作品的最大价值。
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探讨建构主义学说,将“话语”定义为实践,即“他们谈论的对象的系统建构”。这一定义对于文化史学有指导意义,指出了文化记忆对于“话语”这类实践和媒介的依赖。不同的个人和文化通过语言、图像和重复的仪式等方式进行交际,从而互动地建立了群体意识的文化,即诺拉定名的“社会记忆”。本书作者沿袭了这些理论,说:“社会的共同记忆决定了我们对古埃及人以及其他古代人类的形象构建”。
所以,弗洛伊德书桌上的古埃及小雕塑,某一个小物件,也许就是打开文化记忆的一把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