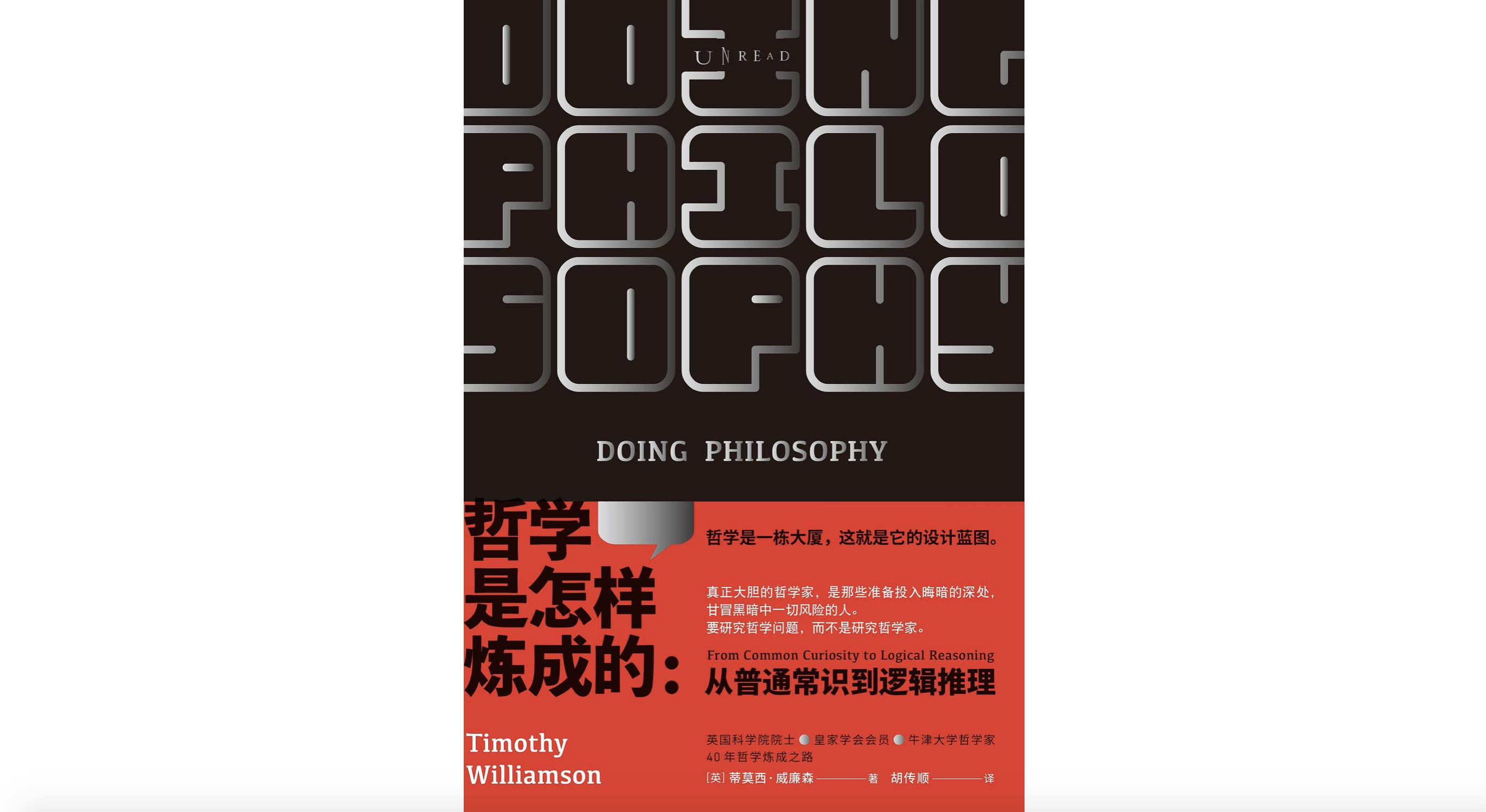作者丨[英]蒂莫西·威廉森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旅行者询问去某地的路,却被告知:“如果我要去那里,我就不会从这里出发。”这个建议是没有用的,因为人们除了从其所在的地方出发,别无他法。这同样适用于任何探究。我们除了从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和信念出发,从我们已经拥有的获得新知识和新信念的这些方法出发,别无选择。
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从常识开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终于常识。我们希望最终能够超越常识。但是,我们能够完全逃离我们所依赖的常识吗?难道我们不把它带到我们的旅途中吗?
想象一下某位遭受持续不断的幻觉折磨的人。他不可能依赖他自己的经验。他甚至不可能依赖别人经验的“传闻”,因为他也可能对那些“传闻”产生幻觉。他已不适合参与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因此,即便最老练的自然科学家也必须预先假定他们的感觉不是一团乱麻。至少,在这个程度上,他们仍然依赖认知的常识方式。
正如自然科学那样,哲学也从来都不会完全逃避它起源自常识。有些哲学家是常识的坚定守护者,或者,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地域是常识的守护者。例如,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84—前322)
、托马斯·里德
(Thomas Reid,1710—1796)
和G.E. 摩尔
(G.E. Moore,1873—1958)
。有些哲学家力求回避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常识,但从来都没有完全成功过。
因此,自然科学家倾向于在幕后保留他们对常识方式的依赖;而哲学家,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更愿意在台前保留它——通常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简单地看待常识的地位。这种循环往复的、自发的与常识的交战,这种断言或质疑,正是哲学方法的其中一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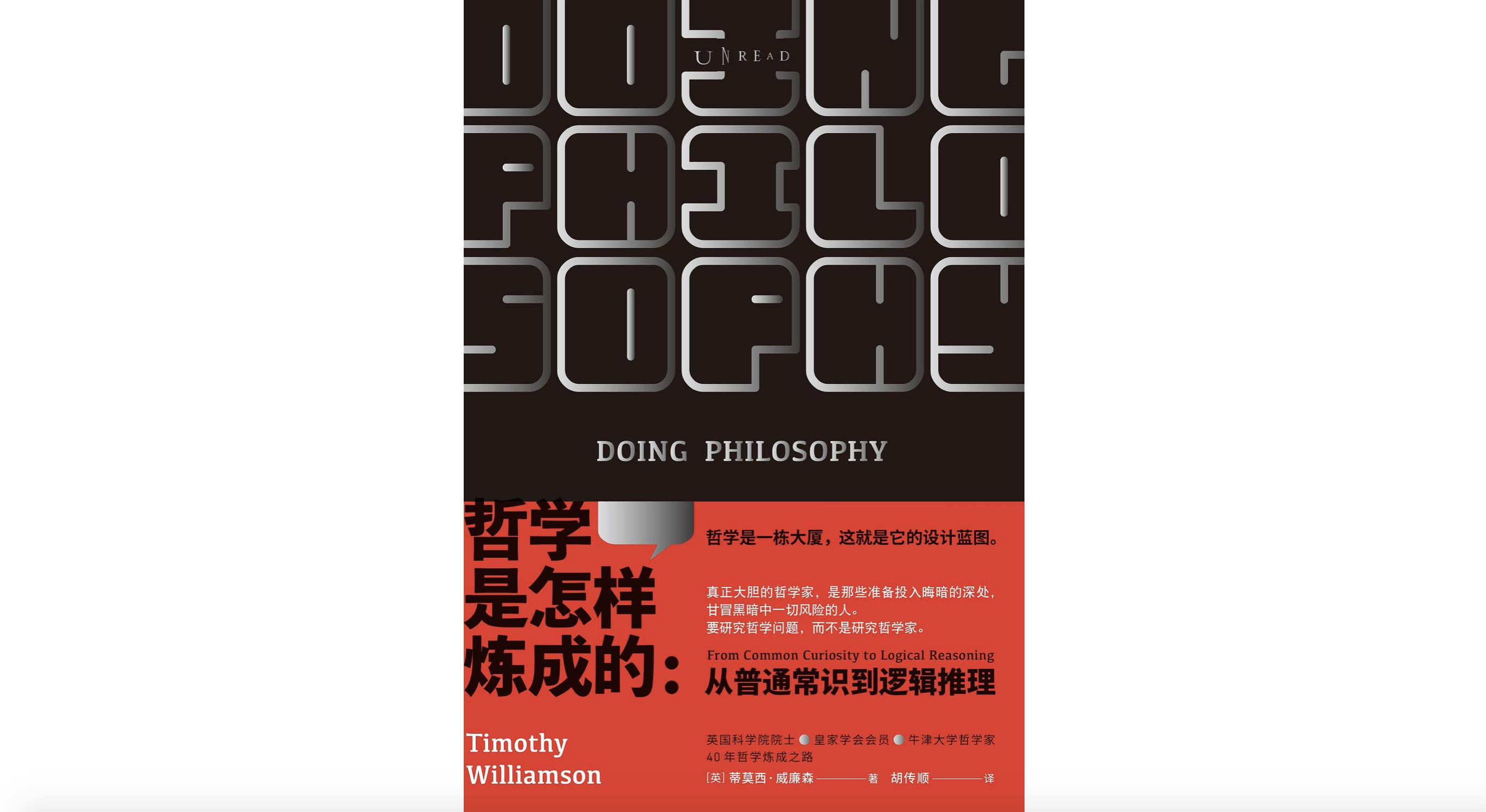
《哲学是怎样炼成的:从普通常识到逻辑推理》,[英]蒂莫西·威廉森著,胡传顺译,未读·思想家丨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何为常识?
常识包括什么?人们或多或少都起始于相同的认知能力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
:我们可以看见和观察;我们可以倾听和耳闻;我们可以触摸和感觉;我们可以舔舐和品尝;我们可以闻闻嗅嗅;我们可以操控;我们可以探索;我们可以记住;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可以用文字和图片与他人交流我们的想法,并且可以理解他们对我们所说和所表现的东西。
以这种方式,我们了解了周围的环境、彼此以及我们自己。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随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长和生活,很多这种认知都是自然而然或不经意间获得,就算没有接受过普通学校或大学的正规教育也一样。
在一个社会里,常识知识,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知道。因此,常识知识在不同的社会并不相同。在现代社会,太阳比地球大很多就是常识知识。在石器时代的社会里,这就不是常识知识。在塞尔维亚语的社会里,单词“crveno”的意思是红色,这是常识知识。在另一个社会,这就不是常识知识,因为在这个社会,很少有人懂得塞尔维亚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常识知识都如此不同。在每一个人类社会里,人们都有头颅和血液,这就是常识知识。
在一个社会里,常识信念就是大部分成员所相信的。所有的常识知识都可能是常识信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常识信念都是常识知识。因为,如果一个信念是错误的,它就不是知识。在一个孤立封闭的社会,每个人都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他们并不真正“知道”它是扁平的,很简单,因为它不是。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知道它是扁平的,但这个信念是错误的。
类似地,在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大部分成员对其他种族的人抱有错误信念。在这个社会,这是常识信念,但不是常识知识,很简单,因为这也是错误的,所以它根本不是知识。即使这个社会的成员都相信他们对其他种族的常识信念是常识知识,这个进一步的信念也是错误的。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社会里,要区别常识知识和常识信念是很困难的,但是,通常其他社会的成员能告之其间差别。
“常识”的概念不仅可以应用于社会中的常识知识和常识信念,也可以应用到产生这种知识和信念的通常思维方式上。
常识问题,哲学问题
像很多其他的动物那样,人类是有好奇心的。我们渴望认知。有很多知识是好事情,它以各种难以预料的方式造就诸多好处。
常识思维包括追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关注非常具体的问题:牛奶在哪里?那边那个人是谁?另外一些人关注较为普遍的问题:你怎么做奶酪?老鼠能活多久?还有些人关注的问题更普遍,包括“是什么”类型的诸问题。一个喝着奶的孩子可能会问:“奶是什么?”她完全知道奶这个单词怎么使用,但她仍然想知道奶是什么。她可能被告知,奶是如何来自乳牛以及其母亲。在这个事例中,答案在她的社会里已经是共同的知识。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的答案可能并不是共同的知识,或者甚至不是共同的信念。例如,有些人可能问:“蜂蜜是什么?”他可能知道蜂蜜是在蜜蜂的蜂巢里被发现的,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例如,当人们被水怎么能够结成冰然后又融化这样的问题迷惑时,他们可能会问:“水是什么?”科学开始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开始于具体种类的动植物的属性这些问题。它们不是关于我们心灵的话语或概念这类问题,而是关于实物本身:奶、蜂蜜、水。我们不可能吃掉、喝下话语或概念。
这些问题还会继续:太阳和月亮是什么?火是什么?光是什么?声音是什么?这样问题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现在把它们认作是科学的开端,同时也是哲学的开端。空间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这些问题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被追问,作为哲学的分支,二者关注的实体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完全不同的感觉,虽然它们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而自然科学是从自然哲学发端的。
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为牛津大学威克汉姆逻辑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丹麦文理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亚里士多德学会和心灵学会现任会长,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等世界各地的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兼职和讲学。
让我们回到哲学的开端看看“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
(Plato,约前429—前347)
曾追问:“正义是什么?”以及“知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他追问的并不是某种
(古希腊的)
话语或概念,而是关于正义和知识本身。当然,它们并不是像奶、蜂蜜或水这样的实物。你不可能有一升正义或一千克知识。
但是,这并不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生物学回答“生命是什么?”
(以及许多类似的其他问题)
这种问题,但生命并不是一种物品。你不可能有一升或者一千克生命。生命和非生命物之间是有区别的;生物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个根本的差异。类似地,在公正和不公正的行为之间也存在着区别;哲学的任务之一
(特别是政治哲学)
就是要解释这个根本的差异。知识和无知之间存在着区别;哲学的另一任务
(特别是认识论)
就是要解释这种根本的差异。常识辨识生命、正义和知识。我们的好奇本性使得我们想要更好的理解它们。
当然,一想到常识的各种差异,有时会使得我们不满意于它们。我们获得常识的日常话语可能太模糊,我们可能会对几种不同的差异犯糊涂,或者仅仅只是标明了它们表面上的不同。这既可能发生在哲学中,也可能发生在自然科学中。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引入新的术语以做出更清晰或更深刻的区分,并且为进一步的探究创造一种更有帮助的架构。常识是这样一种出发点,而不是终点。
作为检验哲学的常识
常识不仅仅是哲学已留在身后的出发点。它还保留了另一种角色,即作为哲学家的暂定结论的检验。我曾经有个同事,他在一次演讲中陈述了他的知觉理论。一位学生指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不可能通过一扇窗户去观看。我同事的理论被常识的知识所驳斥,因为常识是通过一扇窗户观看是可能的。而我一边写,一边通过一扇窗看着树木。
任何一种与常识知识不一致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任何已知的东西都是实情,所以任何与此不一致的东西都不是实情。还有一个例子:形而上学家约翰﹒麦克塔格特
(John McTaggart,1866—1925)
论证了时间是不真实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事发生在其他任何事之后。这就与人们都是在起床之后才吃早餐这一常识知识不一致。因此,这一形而上学理论被驳倒。当代的哲学家通常通过表明某种哲学理论与常识知识的不一致从而排除这些哲学理论。
使用常识作为标准去判断诸种哲学理论,明显存在一个担忧:如果我们把一种错误的常识信念误认为是常识知识,情况会怎么样呢?在一些社会里,人们相信“严刑拷打不是错误的”;事实上,他们相信的是“我们都知道严刑拷打不是错误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哲学家可能会认为他们是通过表明与常识知识不一致从而驳倒了一项人权理论,因为人权理论意味着严刑拷打是错误的。这种“驳倒”难道不是欺骗吗?
这种担忧在于,对常识的诉求恰恰是这样一种伪装,即在判断哲学理论时依赖流俗的偏见。在那些其观点被现代科学所启发的哲学家之中,这样的怀疑特别强烈,因为他们把常识当作是前科学的。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称之为“野蛮人的形而上学”。例如,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有些哲学家否认现在比过去和未来更加真实;他们将不会被反对他们所诉求的常识打动。他们认为,这种常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过时的时空观念。
另一种与常识信念不一致的理论是虚空之中只有原子
(或者基本粒子)
。有些哲学家颇有争议地把这个当成是现代科学的一场教训。根据他们的观点,根本不存在常识中的大型客体这样的事物:没有棍子和石头,没有桌子和椅子。虽然它们显现为大型客体,但事实上,它们是不存在的。现在,极端拒斥常识的诸多危险开始出现。
究竟对谁来说事物显现成为大型客体?也许是人类。对基本粒子来说,事物不会以任何方式显现,因为它没有思想。但是,人类是大型客体,因此,根据这个极端的观点:没有人类存在,更不会有任何事物显现为棍子和石头。没有仅仅是便于运用的像“棍子”和“石头”这样的语词,因为没有人使用它们;事实上,也没有语词,因为语词不是基本粒子。这简直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也对于哲学而言,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自然科学根植于我们进行观察的能力。如果一项科学理论意指,没有任何进行观察的能力,这难道不是清除了它所守卫的科学分支吗?即使人们试图假定观察而没有观察者,他们也会涉及到这种被否定的大型事件。
一种理论,如果它对立于获取有利证据的可能性,那么它就是自我毁灭性的。这同时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既然获得这样的证据最终还是依赖通过感官进行认知的常识性方法,那么,这种辩护性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常识不一致,是有限度的。
常识检验哲学理论这种有争议性的作用提出了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在哲学上,我们必须获得什么样的证据?
不可靠的证据
许多哲学家把现象当作是判断自然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证据的黄金标准。根据他们的观点,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能存有这些现象。换句话说,这个理论应该精准地预测事物将如何向我们显现——或者,至少要避免不精准地预测现象。现在,理论能够在精准地预测现象的同时,仍说某些现象是错误的。例如,理论能预测月亮对我们来说看起来要比星星更大,但同时坚定地补充,事实是,月亮要比星星小很多。
一个更加极端的理论甚至可能预测:对你来说,月亮看上去要比星星大很多,同时补充道,事实是,根本就没有星星和月亮在那里,有的仅仅是你想象的虚构物。这个理论一定预测不到,月亮对我们而言可以“看”起来比星星更小。如果为了符合证据而存有足够的现象,那么最终,你此时此刻必须获得的唯一证据,就是事物此时此刻向你显现的样式。不管你是否正在观看星星和月亮,或者仅仅是幻想它们,你的证据包括这种事实——它向你显现的是星星和一个大得多的月亮。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证据等同于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样式呢?诉求这个等式的是这种思想:关于事物真实的样式,我可能是错误的,但至少,关于事物向我显现的样式,我没有错。但是,关于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样式,我们观察到的真的可靠吗?
要运用现象作为证据以支持或反对一个理论,仅仅是现象的出现,那是不充分的。例如,一个理论预测到,如果你做一项特殊的实验,一个“点”将显现出运动。一旦你做这个实验,运用这个结果支持或反对这一理论,这就要求你判断是否有一个“点”确实显现出运动。判断结果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们人类在做出判断,甚至是在事物向我们显现上,都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点”显现出运动,我仍可能用其他方式说服自己,因为我致力于这个理论,所以,我可能会做出有偏见的判断——“一个点显现出运动”。
不管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我们在对它做出判断上都是不可靠的。有时,我们会弄错。即便我们尽最大努力阻止自己无意识的偏见,我们仍然会失败。因此,在论证中会有瑕疵,而“我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现象,因为除此之外,我可能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为证据设定了一条标准,即使我们没有遇到这些现象。
无论如何,使证据等同于现象违背了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要求证据是可检验的、可重复的、可被其他人公开审核的。根据所有这些测验方式,一个人观察到的短暂现象很糟糕。在这个方面,常识做的更好,因为它是共享的,并且能够被检验。学术期刊上被引用为证据的论文是实验的真实结果,它是以大量的物理术语来描述的。这样的描述比我对周遭环境的日常术语描述要更加精确、更有技术含量,并且比仅仅描述事物向某人显现的样式要更接近日常的周遭环境。
自然科学的这个实例表明,追求一种我们是绝对可靠的证据是徒劳的。不管证据是什么,那些我视之为证据的东西有时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没有什么科学的程序被设计出以提供100%的保证来避免错误。更确切地说,从长远来看,它们是被设计出来以便于纠正各种错误。这是哲学也能够渴望的最好的东西。
哲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在普通人类的能力之上,以多种方式依赖于常识方法去了解这个世界。因此,这两门学科都必须发展诸种策略以回应以下这种危险,即我们视之为知识的东西实际上是错误的。人类的境况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单独依赖于预防,因为偶然的错误势必会悄然而至,尽管我们竭尽所能。在错误发生之后,我们也需要诸多方法以诊断和矫正我们视之为证据的错误。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准许一项对假定的证据提出申诉的权利。
但是,这样的一项权利并不是表明,只要有人质疑一件假定的证据,我们就不把它当作证据了。这将使未经证实的质疑具有决定性意义,放纵淘气的怀疑论者逐渐中止哲学和自然科学——仅仅通过机械地质疑任何成为证据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这值得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位批判者必须提供好的理由以质疑一件具体假定的证据。这些理由本身最好基于证据之上,经得起反过来的质疑。
常识的可靠性
根据本节中的一幅图片,如果常识完全脱离现实,那么,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没有什么机会使得我们接触到现实,因为这两门学科最终都太过于依赖认知的常识方法。但是,认为常识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的假设是否太过乐观?难道常识信念不比正确,甚至近似正确更接近实际上的有用吗?并且,一个社会或时代与另一个社会或时代之间常识上的各种差异,难道不是表明他们的常识并不能反映现实吗?
这些怀疑的论证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正确的信念比起错误的信念,更倾向于在实际上的有用。其次,我们倾向于,在常识上发现分歧比发现一致更加令人惊奇,也因此更加有趣,而一致是预料中的无聊。由于我们关注的是分歧,与所有幕后的一致相比较,我们很可能过高地评估了分歧的程度。经验表明,任何彼此保持联系的两个人类群体将设法达成交流:常识上的这些差异对交流来说并不太重要。
如果人们寻求达到了实际上的有用性而不是真理的有关常识的真实事例,最好的观看对象就是非人类的动物,因为人类的虚荣心或沆瀣一气并不会使我们对它们有什么偏见之心。想一下,一只正在追捕一群黑斑羚的猎豹。这两种动物当然都有它们各自的学习生存环境的常识方法。这些方式完全脱离于现实,有道理吗?根本没有。对于猎豹和黑斑羚这两种动物来说,知道是否有其他种类的动物在附近,如果有,在哪里,这确实是事关生死的事情。它们已经进化到善于获取这样的知识。
我们通常将某只猎豹或黑斑羚如此行动的原因归因于这些知识,从而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像我们一样,它们也是不可靠的,并且有时会有错误的信念。一只黑斑羚可能错误地相信,没有猎豹在附近。但是,说明这是错误的信念就在于这只猎豹的技巧或运气,而不在于这只黑斑羚完全脱离现实。自然而然地,猎豹和黑斑羚的知识主要关注对它们而言极小部分的现实的实践利益,但在这个限度范围内,它令人赞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南非看到一群黑斑羚与一只猎豹互动的场景。
一只猎豹与一群黑斑羚。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要否定非人类的诸种动物的常识知识是不可能的。正如同从生物学的角度否定人类这种动物的常识知识也是不可能的。把这样的知识归因于我们自己,并不涉及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偏爱。有很好的证据支持这点。
因此,对违背常识的哲学理论进行测试的实践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同样,质疑所谓常识知识的实践也拥有了这样做的具体依据。在实践中,要恰当的说出什么应该算作是我们的证据的一部分,可能是困难的。但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在原则上,证据总是可以被质疑。
本文选自《哲学是怎样炼成的:从普通常识到逻辑推理》([英]蒂莫西·威廉森著,胡传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由未读·思想家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