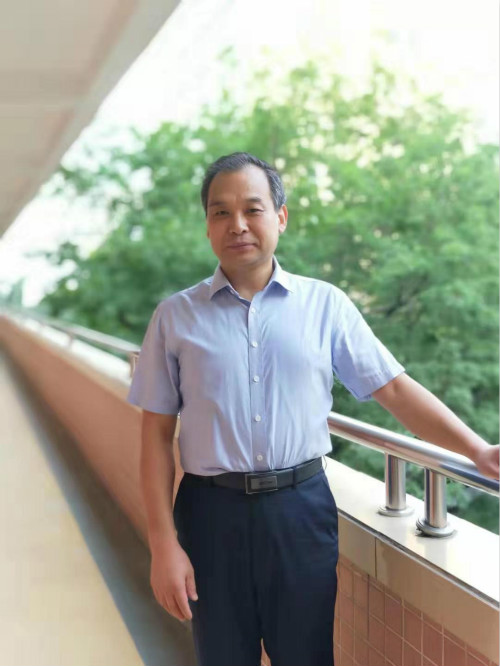【编者按】
义宁陈氏源出客家,雍正年间始由福建上杭迁至江西修水,属于被土著士绅排斥的族群,其家族用了百年时间从“棚民”跃升至乡绅;直到陈宝箴中举,才为家族初获功名,以后更因缘际会,成为独掌一方的大员,可说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再到第二代的陈三立,尤其是更下一代的陈寅恪,才算在文化上取得了成功。
义宁陈氏是如何“耕读传家”的?又是如何从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的?针对上述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陈寅恪家史》作者、广东行政学院教授张求会,请他谈谈这部“陈寅恪前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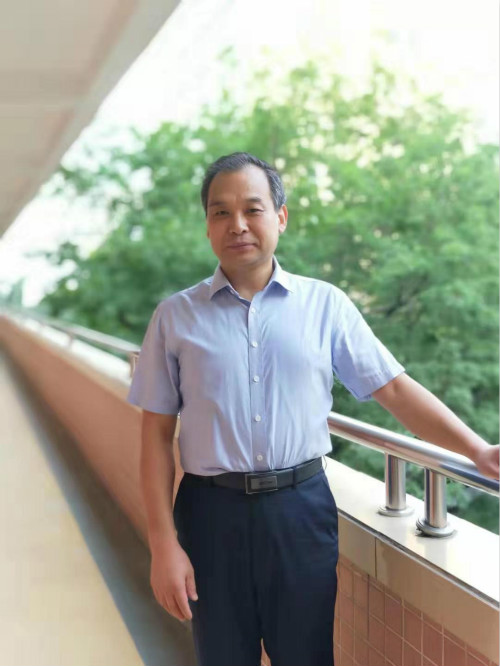
张求会
澎湃新闻:
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启了您的义宁陈氏研究?
张求会:
我的祖籍是安徽省含山县,1973年随母亲迁入江西省九江地区的永修县,与我父亲团聚。1958年,我父亲因为大饥荒从安徽以“盲流”的身份逃到江西。可以说,江西收留了我们一家,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永修县位于修河(修水)的下游,修河在永修的吴城汇入鄱阳湖,再流入长江。修水县在修河的上游,永修县在修河的下游,套用一句老话,我也曾经和义宁陈氏“同饮一江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缘分。
我的中学是在永修县内一个叫做军山的小镇完成的,连续几年,每次上学都是从杨家岭火车站沿着铁路走到军山站,脚下的这条铁路就是南浔铁路。杨家岭位于南昌和九江的中间,往北挨着军山,往南挨着涂家埠,涂家埠正是南浔铁路跨越修河的重要车站。一句话,我移居的地方、我走过无数次的铁路,都是南浔铁路总理陈三立当年足迹所及之地。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缘分。
更重要的机缘,是我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碰到的一次机会。1993年我从江西考入广州的华南师大,跟随管林先生学习中国近代文学。1994年,管先生受到江西方面召开陈宝箴、陈三立研讨会的邀请,他当时已经是华师的校长了,事情太忙,无法参加,就让我摸一摸陈氏父子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参加学术会。我遵命作了一次基础性的摸排,这才发现相关研究很不到位,各种工具书(不少还是权威辞典)连陈三立的生卒年都互相矛盾。后来我代表老师去开会,还应邀作了发言,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还好没有瞎说。回广州后,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非常宽容、开明,同意我选择义宁陈氏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从此我就一头扎进去了,再也没出来,不知不觉做了二十多年。可以说,业师管林先生是我从事义宁陈氏研究的引路人。
澎湃新闻:
陈寅恪的先祖陈公元为何在康熙年间从福建迁移到江西?您曾经到修水县实地考察过,当地的情况如何?
张求会:
我是1997年第一次去修水的,2011年第二次去,最近一次去是在2016年。后两次去,个人所见所闻虽然很有限,仍能感觉到当地在不断地发展,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体现。第二次去的时候,陈家大屋已经在几年前升格为省级文保单位,县里当时正在着手开发其中的旅游文化资源。第三次去,陈家大屋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开发的事情仍在酝酿。修水县原本计划在2019年11月举办义宁陈氏文化园的开园活动,因为忙于“脱贫摘帽”,所以临时改到了2020年。也就是说,修水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长期属于贫困县,这种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可耕地较少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可以往上远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义宁陈氏的先辈之所以在清朝雍正年间(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从福建上杭迁居到江西修水,以往的说法是上杭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大,但是根据学者刘经富教授的研究,当时修水的地理、经济、文化状况未必就比上杭好。我们都知道,移民往往是“多因一果”的复杂现象,目前只能说陈氏这次迁移的具体原因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究。
澎湃新闻:
迁至江西后,陈公元、陈克绳、陈伟琳三代人都选择“耕读传家”,这种三代人的“耕读传家”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百年间他们做了何种努力,使义宁陈氏从“棚民”跻身地方名流?
张求会:
义宁陈氏的“耕读传家”不是说他们没有选择科举,说白了,是考不中,不只是一个人考不中,而是几个人或者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碰到这个困境,不少人还是多次考不中、一辈子考不中。难得的是,陈家数代人没有放弃科考,只要生活尚可维持,条件稍稍具备,务农之余必须读书。“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读”才是抬高身份、改变命运的惟一通道。
放眼来看,“耕读传家”可以说是中国最悠久、最优良的传统之一,各朝各代、南北各地都相当普遍,陈家三代人应该是主动选择了这一做法。但是,在修水这样一个山多田少、农作物产量偏低、商品贸易不够发达的山区,“耕读起家”的概率估计不会高到哪里去,靠种田发家致富的难度只会比其他地方大得多。因此,各种碑铭、传记关于陈家“耕读起家”的说法难免夸大其词,未必可信。
我的朋友胡文辉在《陈寅恪家史序》中推测义宁陈家凭借种植业和商业取得了成功,这个说法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是启发了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修水具有丰富的竹木资源,将竹木扎成竹排、木排,顺修河而下,贩运获利,也是一种重要的营生。我在修河下游的永修县前前后后生活了18年,亲眼在修河上见过这样的竹排、木排;陆路上禁止偷运修水、铜鼓等山区竹木的木材检查站,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了很多年,胆子大的人冒险偷运木材盈利的事情一直没有中断。因此,我推测陈家或其他家族可能从事过竹木贸易活动,并借此获得远远超过种植业的利润。义宁陈家从事种植业,确凿可信的记载,有种稻、种蓝、种茶等;但是从事商贸活动的记载,几乎没有发现。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行医是陈家从“农”成“士”的阶梯,这个说法值得怀疑。陈家有不少人懂得医术,这个确实不假;陈伟琳游历北方,依靠沿途行医获取盘缠,也很有可能;但要说行医帮助陈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跃升,很难自圆其说。
此外,义宁陈氏家族属于客家民系,客家人在客居地难免遭到土著的排挤、打压,生产、生活、科举等等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由此激励客家人更加勤奋、顽强,不屈不挠地争取合法合理的社会政治地位,这种情况在各地都存在,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相比而言,义宁陈家数代人在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子弟的教育,更加注重提高家族在客裔族群中的地位,同时,与土著乡绅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包容、开放一些,而不是一味地敌对或排斥,这一点可以称为陈家的过人之处。
澎湃新闻:
陈宝箴是义宁陈氏第一位全国性的“杰出人物”,他的成功与太平天国关系密切。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同为客家人,洪秀全和义宁陈氏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您能否详细讲讲他们之间的区别?
张求会:
时代在进步,研究在深入,看待这个问题也要与时俱进。陈宝箴家族经过百余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从棚民到乡绅的跃升,想不到在他父亲陈伟琳那一代遭遇了太平天国运动,如果帝国上下真的天翻地覆,陈家的努力必定付诸东流,因此对于这一巨变作出回应完全正常。
客观地说,乡绅与官僚制度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成为乡绅纷纷投笔从戎组建民团抵御太平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太平军在局部地区(包括义宁州城)的道德放任、纪律松懈甚至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也难以避免地引发社会各界自觉自愿的反抗。
除此之外,乡绅与天王之间、民团与团营之间所进行的战争,更是一场关系到正统价值观念、社会准则以及现存社会秩序命运的殊死搏斗——这一方是传统文明的正统而自觉的承受者和延续者,那一方却是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挑战者和改造者。太平军对传统社会准则、制度、信仰、文化及其载体,或大胆摒弃,或彻底摧毁,加上对外来教义来不及认真吸收、有效改造,使得太平军占领控制的地区与广大乡村之间因此出现文化和情感上的鸿沟,一步步走向崩溃的清王朝反而成为一般正统士子保存文化传统的某种寄托。此种情形,诚如陈寅恪所言,“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文化无形又有形,“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赤县神州遭受“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之际,深受文化传统熏染的一代文人士子之所以甘于“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实际上往往另有待发之覆。洪秀全与义宁陈氏的不同选择,应该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多个维度予以综合考量,而不能再简单地归结为政治上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
清朝咸丰初年,陈伟琳及其长子陈树年、幼子陈宝箴,父子两代人都直接参与了防御太平军进攻义宁州的军事行动。后来,陈宝箴投奔席宝田、曾国藩等湘军统帅,继续参加镇压太平军的诸多战役。义宁乡绅自办团练,辅佐官军抗御太平军、收复州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走势,陈氏父子功不可没,由此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包括曾国藩等湘军大佬的垂青。可以说,在曾国藩大营中参幕,继而成为湘军集团的一员(尽管不是最核心的成员),是直接将陈氏家族从竹塅山区带向广阔天地的最重要一步。我在《陈寅恪家史》里把这个过程称为“时势造英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说“时势造英雄”,但是真正能够把握机遇甚至影响时势的毕竟还是少数。陈宝箴之所以能够以客裔举人的身份脱颖而出,通过军功一步步走向仕途,最终在戊戌变法的时代浪潮中达到人生的最高点,除了时代使然,的确和他具有良好的文化根基、坚韧不拔的个性、宽阔恢弘的胸襟等有着很大的关系。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被罢职,1900年陈宝箴病逝,陈三立在为父亲撰写的《行状》中,尽管受时局所限,未能畅所欲言,也难免有部分谀墓之词,但仍然为后人留下了一篇最重要的陈宝箴传记。陈三立在《行状》里这样称誉自己的父亲:“性开敏,洞晓情伪,应机立断,而渊衷雅度,务持大体,不为操切苛细。少负大略,恢疏倜傥豁如也。及更事久,而所学益密,持躬制行,敦笃宏大,本末灿然。”换而言之,陈宝箴的聪明才干和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诸多重要师友的认可、帮扶,为自己和后代积累了十分丰厚的人脉资源。
陈宝箴
澎湃新闻:
陈宝箴对于维新变法的理念是否来自于曾国藩与郭嵩焘?他的理念与康梁等人有何不同?
张求会:
陈三立在给父亲写的《行状》里这样说:“府君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师友交游多当代贤杰,最服膺曾文正公及沈文肃公”,“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这里的“学宗张朱”,把陈宝箴治学、治事的源头远溯到了张栻和朱熹,这其中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套话的成分,但是永嘉叶适重“事功”、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姚江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至少可以说这些主张很对陈氏父子的脾胃,容易引起共鸣,有机会时付诸实施,这一点毋庸置疑。
湘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到了清朝咸同年间,中兴名臣曾国藩借着湘军声势的崛起、壮大,坚持传播“以礼调和汉宋”的主张,强调时务致用、兼收并蓄,成为当时经世学风的主流。郭嵩焘的经历、主张对陈氏父子的影响,更为人们所熟知,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生前的遭遇,现在看来,未尝不可视为已经预示着“经世致用派”或“中体西用派”最终破产的命运。
不过,相比之下,晚清危如累卵的时局以及由此而来的亡国亡种的危机,才是促使陈氏父子投身维新事业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归入“洋务派”阵营还是“维新派”队伍,一直在研究界存在着争议。“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区别,可以归纳出无数条,然而,当事人当年是否有此意识,是否认同后人的划分,我看则未必。“师夷长技以制夷”(器物层面大胆吸收外国之长)大概是一致之处,是否涉及制度改革(尤其是政体、国体等敏感领域的变革)大概是研究者区分二者的重要界线之一。这次重写《陈寅恪家史》,我保留了凸显维新派内部激进、稳健两个阵营矛盾的若干章节,又特意标举已故历史学家黄彰健的观点,既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也是借此说明后来的划分其实并无多大的意义。
澎湃新闻:
对于维新变法,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的理念有何区别?
张求会: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同心协力,共同完成湖南维新各项创举,陈灨一评价说:“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王闿运则用戏谑的口吻,将之归因为“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这是父子二人维新理念一致的地方,但是两代人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比如,谭嗣同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说,就指责陈三立“平日诋卓如、诋绂丞,(及力阻不许聘康南海来湘。)则其人亦太不测矣!而又往函丈处陈诉,岂欲出死力钤束嗣同等而后快耶!”黄彰健以此作为证据,认为陈宝箴对于维新派内部激进言论的容忍度比陈三立为高,陈三立比他父亲显得相对保守一些。与此同时,黄彰健又对父子二人的委曲求全给予了解之同情:“民权平等之说,在戊戌年,本惊世骇俗。陈三立为了他父亲的官运前途,欲采取一较稳重之途径,此亦人之恒情,不足异。即令对陈宝箴来说,行民权以应付大难,那仍是万不得已的举措。在情势正常时,还是走忠君的老路,官运可以更亨通。陈宝箴的立场本可以有妥协性,而这也可能是张之洞致电干涉及徐树铭弹疏上后,陈改变他对新党的态度的主要原因。”
黄彰健还这样解释陈宝箴《致王先谦函》流露出的难言之隐:“在光绪戊戌年,士大夫重视忠君,民权平等之说已为旧党所不能接受,何况他们有‘悖逆’叛君的言论?陈氏既不能明白承认梁氏批语意存‘叛逆’,又不能明白向王先谦等人解释,此系康党为了应付国家危机所作的‘亡后之图’,更不能向王解说陈已同意自立民权的主张。陈不能同意新党于前,翻脸不认人而惩罚新党于后。陈因此只能取康最近言论,谓康党已放弃民权主张,康党已投诚,而希望旧党不予追究;并说北宋之衰亡与党争有关;康、梁、谭、唐诸人系国家才俊,仍应爱护维持,使为国家服务。……陈此信所论,虽由于顾虑到自己政治生命的安全及同寅世谊,仍可说是老成谋国,无可非议。”
陈三立
澎湃新闻:
义宁陈氏对教育特别重视,在主政湖南期间,陈宝箴父子兴办的时务学堂为维新输送了不少人才。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是否源于家族的影响?陈宝箴父子兴办时务学堂,注重怎样的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求会: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兴办时务学堂,受到家族历代重视教育的影响,这样说肯定不算错。不过,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为湖南维新大业培育人才应该是开办时务学堂最直接的动力。
梁启超赴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前,康有为曾与之商议教育方针,师徒等人最终确定的办学宗旨是:以“急进”之法,宣扬“彻底改革,洞开民智”,而“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康门弟子随即对年轻的湖南士子展开了旨在“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的启蒙式教育。梁启超以康有为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教学内容侧重培养学生具有变法维新的意志,阅读儒家著作及历代治乱兴衰的记载,参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研求危机紧蹙之际救亡图存的对策,尤其醉心于民权平等之说。曾在时务学堂肄业的学生,不少人日后都在不同的领域成就了一番名垂青史的伟业,其中,既有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豪杰,也有终生奋斗于进步事业的民主志士,还有创造一代学术高峰的国学大师。守旧士绅将时务学堂视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其实是对时务学堂的最好评价。客观地说,时务学堂当年和日后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当然凝聚了陈宝箴父子的心血和汗水,但在整个过程中,陈氏父子和时务学堂诸生之间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关系,不需要人为地拔高放大或加冠加冕。
澎湃新闻:
戊戌变法的失败对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有何影响?
张求会:
戊戌政变,彻底改变了义宁陈氏的家族命运。陈宝箴虽然并非慈禧赐死,但仍然可以算得上戊戌政变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陈三立同样遭遇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名誉受污等等精神打击之外,家庭生计也日渐困顿,甚至一度陷入难以为继的极端困境。尽管戊戌政变确实在日后为义宁陈氏增添了耀眼的光环,但在其时其地,深陷其中的每一个当事人,品尝到的估计只有苦涩和辛辣。政变后,义宁陈氏后人退出政坛,转而在文艺、教育、学术等领域经营人生;与之相伴的是,对于激进言论的反感甚至反抗,也从政治变革转移到其他领域,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就可以说渊源有自。
陈寅恪
澎湃新闻:
陈三立为何不继续仕途,转而诗文创作?是历史环境使然还是一种个人选择?
张求会:
与陈宝箴相比,陈三立确实缺乏游刃于官场所必备的一些素质,倒更像一位名士习性浓厚的诗文家。对于不谙宦术这一点,陈三立很有自知之明,多次在诗里自我调侃甚至嘲讽。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清廷开复陈宝箴原衔、开复陈三立原官,那一年陈三立五十三岁,尚可称得上年富力强。现在看来,他之所以没有继续走仕途,应该和戊戌政变留下的阴影有关,也应该和这一份自知之明有关。
不过,陈三立并未就此与官场绝缘——事实上也做不到这一点。第二年(光绪三十二年),端方调补两江总督后,就曾延请陈三立入幕。此后,陈三立在参与筹建南浔铁路期间,也曾利用与端方、陈夔龙(江苏巡抚)、瑞澂(上海道道台)的特殊关系,帮助自己和铁路公司摆脱困境、收回权益。传说陈三立在戊戌政变后无意仕进,而是一心一意沉浸于诗文创作,难免有夸大的成分,毕竟他要为一家大小的衣食着想,要为后代的前途着想。
当然,对于诗文创作,陈三立的确乐此不疲,在寄托情怀、慰藉身心的同时,诗文成就既能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又能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应邀撰写寿文、寿诗、碑铭、题辞、序跋等等,绝对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创收手段。
合而言之,陈三立在戊戌政变后转而以从事诗文创作为主要职事,既是个人兴趣的自然顺延,也是扬长避短的最优安排,同时还是维持生计、获取名誉的必由之路。
澎湃新闻:
从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来看,陈家是一步步从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的。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向?
张求会:
陈氏三代人一步步从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这是胡文辉在《陈寅恪家史序》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我很感谢文辉为我这本小书写序,这句话也被我借用在扉页显著的位置。在序言中,文辉的原话是:“科举的废除,不仅意味着士人立身托命之途完全改易,也意味着学问与政治完全分作两途。在这样的背景下,陈门子弟本来就在教育上异常用力,则选择学问一途自是顺理成章。而且,陈宝箴既沦为政治罪人,其后人弃政从文就更易理解了。”此外,他在序言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在近代社会转型阶段,’商而优则学’的固然不少,‘仕而优则学’的亦大有人在,‘商二代’和‘官二代’走上学问之途的概率都相当大。这样来看,陈门子弟的成才也未出乎时代大潮之外。陈三立一生,为政未成,从商亦未成,可谓馀事作诗人,只算是半吊子的过渡人物;而他的子辈,陈师曾以画名,陈寅恪以史学名,陈方恪以诗词名,则完全从政治世界走向了文化世界,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显而易见,文辉“更愿意从社会因素而非精神因素来理解义宁陈氏”,他认为这样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不易落入“浮泛的颂扬套路”。文辉学识渊博、眼界高远,是我钦敬的师友。他的这一论断,我深表赞同。当然,除了时代变革、社会变迁的外部影响,肯定不能忽略陈氏家族百余年间延续不断的诗教传统的内在影响。换言之,社会因素固然直接、显豁,但精神因素绝不能因为间接、隐秘而被否定。一句话,精神基因、文化基因虽然检测不出来,但谁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和作用。
张求会著《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11月
澎湃新闻:
《义门陈氏家法》对几代义宁陈氏的为人处事有何影响?
张求会:
修水怀远陈姓历次所修宗谱里记载的家规(《义门陈氏家法》)一共有三十三条,作者是唐朝人陈崇。序言开宗明义,点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第一条,继续强调确立纲纪的重要性。三十三条家规,可以说涉及自然经济时代家族生产、生活、教育等方方面面,与“耕读传家”的深厚传统可谓高度契合。家训有十二条,包括“孝父母”“笃友恭”“端士习”“勤本业”“崇节俭”“尚忠厚”“黜异端”“睦宗族”等。
综合而言,家规、家训中的一些合理性内容,比如重视纲纪、注重教育、友于兄弟、忠于职守、崇尚节俭、不尚异端等等,在义宁陈家数代人之间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而家规第二条、第三条关于选任“主事”“库司”的灵活规定,最能看出民主作风,最能体现变通精神。无论是陈宝箴从政,陈三立以诗文为生,陈寅恪治学授徒,都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看到这些家规、家训的影子。
澎湃新闻:
既然本书名为《陈寅恪家史》,为何不写陈寅恪的传记?
张求会:
这个问题,我在后记里其实已经作了回应,这里再作一点补充。2000年《陈寅恪的家族史》问世后,就有读者和朋友建议增写衡恪、寅恪兄弟各章。2007年再版,出版社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要求做“挖补”式的修订,故此只能微改微调。应该说,在这期间,义宁陈氏研究渐渐成了“显学”,所能使用的材料已经越来越多。而时隔十余年的现在,恪字辈兄弟的著作,除了登恪以外,都有专集出版。作为一本家族合传,确实应该补入恪字辈兄弟。考虑再三,这次重写还是维持了《陈寅恪的家族史》原有架构,而将恪字辈相关言行作了增补,仍旧穿插于前辈生平之中(比如《岁在庚寅》一节就是典型,《铁路经理》最后一部分添入陈隆恪出任南浔铁路总理,也是如此)。
取舍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恪字辈兄弟,自然以陈寅恪最受瞩目,写起来难度最大,写出来也应该最有看头,恰恰是对他的研究(包括生平,遑论其他)最需要完善或突破。因此,我觉得目前还不是为陈寅恪作传的最佳时机,撰写陈氏家族合传的外在条件也还不够成熟。当然,我自己对陈寅恪的各种专门之学一窍未通,研究不到位,储备不丰厚,确确实实没有为他作传的底气,这不是自谦,而是实情。我在《陈寅恪家史》后记还说了第二点理由:“陈寅恪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是陈氏本人所撰家史,纵为残篇,大体犹存,文中虽叙及己身之婚姻,重心仍在彰显家世与国运之关联,于其昆仲并无涉及。因此,《陈寅恪家史》不为恪字辈单独立传,窃以为亦可谓有例可循。”即便读者认为我是在找借口,我也还是认为这样处理未尝不可,因为家史的范围(上限、下限)确定到哪里比较合适,也没有固定的标准。
此外,199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影响至今;2013年,此书修订再版,依然受到各界关注。其间,2010年,三联书店推出陈寅恪三个女儿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试将两种著作合而观之,陈寅恪一生的行迹大体上已经清晰明了。换言之,这两本书可以看作“陈寅恪本传”,《陈寅恪家史》可以称得上“陈寅恪前传”。在很难超越前面两本书的情况下,如果按照《家史》各章的写法去写陈寅恪传记,既写不出什么新意,体例上也不大相合。相比之下,还不如一心一意发挥好“陈寅恪前传”这一功能更加务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