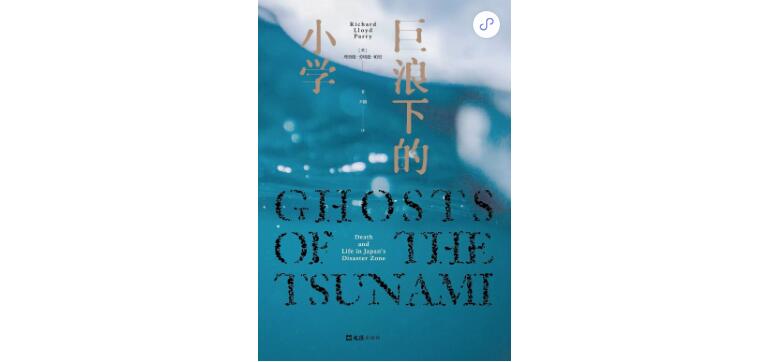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前不久,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性侵的民事诉讼案作出裁决,判决伊藤诗织胜诉。这场被称为“日本之耻”的性侵案历时四年之久终于有了交代,而伊藤诗织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首次公开具名指控职场性侵的女性。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纪录。伊藤诗织的勇敢背后,恰恰是日本社会隐忍、沉默的大多数。在2018年#Metoo运动席卷全球之时,伊藤诗织是极少数愿意打开“黑箱”的日本女性,西方媒体甚至就此撰文发问:一向被视为亚洲文明之光的日本,在面对性侵这样的社会不义之时,为何表现得如此克制与沉默?
最近出版的《巨浪下的小学》似乎也在回应同样的问题。这本书讲述了发生于日本“3·11”大地震的真实故事,作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是《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在日本居住16年之久。
地震发生之后,理查德·帕里持续六年追踪调查大川小学74名学生在海啸中遇难的原因。他想要弄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孩子的死亡?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遵守秩序、服从纪律的日本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作者,追溯八年前这场悲剧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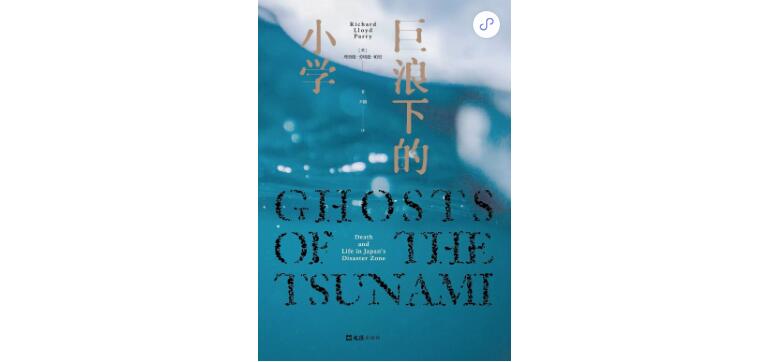
《巨浪下的小学》(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著,尹楠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七十余名学生遇难,
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2011年3月11日,一场大灾难发生于日本东北部。约1.8万人死亡和失踪,这是日本自二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对生活在日本的人来说,地震带来的震感可谓司空见惯,防范措施也早已熟稔于心。日本的地震抗灾方案,也常被视作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然而,“3·11”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啸,还是让日本人猝不及防。
“3·11”地震后为逝者哀悼的人群。
灾难发生之时,旅日作家李长声正在日本,他在近日的活动中回忆起八年前的那一天,仍然心有余悸。很多日本人低估了地震之后引发海啸的风险。“当时民众普遍有这种麻痹思想,因为北上川的河流是自南向东流的,很多人认为即使发生那么大的海啸也不会到他们这里来。”
大川小学坐落在靠近北上川河谷的海岸附近,位于距离东京300公里外的宫城县石卷市。日本在这场地震中总共有75名学生遇难,占到死亡总人数的2%,然而其中74人都来自大川小学。这样的伤亡情况显然不同寻常,作者理查德·帕里也发现其中可能有蹊跷之处,这成为他最开始追踪调查的起点。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巨浪下的小学》作者。
让帕里感到惊讶的是,恰恰是学校老师严格地按照避难手册的指示引导,夺走了这些无辜孩子的生命。这些学生们本应能轻松逃过这场灾难。在地震发生与海啸来临之间,相隔整整50分钟。在学校的操场后面,有一座小山,从学校附近爬上去只需要5分钟。然而,大川小学的副校长没有这么做。尽管已经多次收到了海啸警报,但他仍然决定让孩子们留在学校的操场上。副校长之所以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是因为学校的灾难应急手册中有着明确的指示。针对海啸,手册中写道:“主要疏散地点:学校操场。发生海啸时的二次疏散地点:学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园。”应急手册的纰漏与教条式的执行让这场天灾成为了本可以避免的人祸。
意见的分歧:
为什么家长不愿追究校方责任?
事故真相的披露,并没有终止作者的进一步调查。事后的责任追究更是让这位来自英国的资深记者难以理解。在官方的情况说明会上,大川小学的校长向家长们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尽管他的态度表现非常诚恳,但同时也淡化了自己的责任,将这一切归结于疏忽大意。没人愿意承认这场“事故”源于失职,更没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从而损害自己所在机构的声誉。一部分家长无法接受校方的推脱其词。他们质问事发当天校长为何不在学校,事后又为何不参与救援。然而,另一些家长则同情校长的遭遇,他们认为这样大声地喊叫、质问伤害了家长与学校、政府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在灾难中失去了孩子。
同为受害人的家长,俨然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团体。在一方看来,与官僚系统的对峙阻碍了善后事宜的工作。其中一位家长直美在海啸之后一直在淤泥之中挖掘尸体,希望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为此她还特意考了挖掘资格证书。“我也对教育委员会很不满意”,直美告诉作者,“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我们需要他们的合作,才能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纪录片《生于3·11那一天的孩子们》(あの日 生まれた命 2014)画面。
2011年“3·11”地震发生之后,在各方媒体的地震新闻报道中,日本民众井然有序的自我救助一直被视作他国学习的榜样。“我的一个烦恼是不时要谢绝馈赠食物”,作者在书中写道,“这些刚刚失去家园的人会因为没能款待客人而表示歉意,流露出略带哀痛的诚挚之情。虽然从汽油到厕纸,几乎所有东西都长期短缺,但没有人明目张胆地趁乱打劫,也没有商人趁机涨价。我也没见到打架斗殴、大声争吵或意见分歧,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人自怜自伤。”
大难中人性的闪光触动了作者,但作为一名外国记者,距离感让他产生了另一个质疑:政府去哪里了呢?如果西方国家发生类似灾难,受灾民众会迅速而敏锐地想要知道:政府在哪里?而在2011年的日本,这是一个极少被提到的问题。幸存者的互帮互助虽然是道德上可以预期的行为,但在作者看来,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对官方的援助不抱有期望。五十多个家庭在这场海啸中失去了孩子,最终只有二十三个家庭决定站出来起诉政府。直到申诉有效期的最后一刻,这二十三个家庭才正式递交了起诉书。显然,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克服各方面的反对声音。
为这些家庭打官司的律师非常理解家长们的顾虑,“它不是那种显而易见或明确的伤害,但人们能隐约感觉自己受到指责。如果当事人有亲戚在当地政府工作,那个亲戚的日子可能就不太好过。在学校,当事人的儿女会被人指指点点说是闹上法院的人的孩子。网上也会有尖酸刻薄的言论。”
日本人的宿命论:
“坚忍”是一种美德吗?
在日本,随处都可以听见“加油”(Ganbarō)这个日语单词。它是一个鼓励人们克服困难和挑战的劝勉之词:最直接的翻译是“不屈不挠”或“竭尽所能”。灾后日本的车站和公共建筑上,时常可以看到印有“东北加油!”的横幅。这让作者理查德·帕里感到不解。因为,通常当孩子面临考试或运动员参加比赛时,你会对他说“加油”。但作为灾后表达哀悼和同情的方式,“加油”这个词在这种语境下就显得异常别扭。
作者在受访时提到,日本人在本能上对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感到抗拒。因为这会视为违背了社会的潜规则或不成文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依靠法律途径的个人,往往会被看作缺乏坚忍的品格。就像俄罗斯人笃信黑暗宿命论一样,崇尚忍耐(nintai)或坚忍(gaman)是日本人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的国民特质。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这种国民特质似乎与日本泛神论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在民众间普遍的宿命论态度。把死亡视作有不可抗力在其后操控,顺应天命而不是“逆势而为”,这样悲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
加拿大哲学家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也曾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到达日本东北地区考察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在他最近的著作《平凡的美德》(The Ordinary Virtues)中,叶礼庭探讨了日式的“坚忍”和“顺天应命”是否应被视作普适的道德价值。
叶礼庭《平凡的美德》(The Ordinary Virtues)封面(哈佛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习惯于忍受压抑的人更愿意未雨绸缪,为可能的不幸做好预防措施,并从经验中学习,减少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确实发生了灾难,就应当怀抱希望和热情去应对,而不是以传统的宿命论去忍受。这种“坚忍”实际上无异于一种“残忍的道德实践”,与其说“坚忍”让灾难的受害者成为了英雄,不如说是“坚忍”让他们将自己抛给命运,同时为其他的旁观者置身事外留出了时间和空间。
这种宿命论的态度造成了日本人复杂的两面性:在天灾面前临危不乱,有序避难,自发地维护社会秩序,这是报道中常见的、最好的日本;面对权力的腐化与人性之恶,选择被动地顺从,压抑自我,逃避责任,这是被遮蔽的日本的另一面。“在那场灾难过后的最初几天里,坚忍就是将混乱不堪的难民团结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作者在书中写道,“但也正是这种力量阉割了政治,让日本人觉得个人权利无用,对国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担个人责任。”
“无责任体系”与沉默的大多数
责任伦理的失位,似乎成为了日本二战以来始终难以消弭的心结。日本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曾在战后考察日本的国民性问题,他称之为“无责任体系”与“压抑的转移”。面对政治决策和军事行动上的失败,日本人始终不愿意承担终极的责任。在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上,丸山真男发现战犯的主体责任意识非常薄弱,在与德国纳粹战犯的对比中更为显得突出。这不仅仅归咎于军国主义分子的恬不知耻或道德沦陷,而是整个国家体制性颓废的象征。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日)丸山真男著,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版
丸山真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近代主体意识。主体性的缺失是日本国民的整体性问题,即使是国家统治者也不例外,作为最高领导人丝毫没有作为独立的个体承担起自身行为责任的自觉,而是将一切都归于职务和权力地位,基于与国家权力的合一,基于对以天皇为首的权威等级体系的依附。一旦剥离其对权威的依存,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每个人都是脆弱卑微的存在。
从二战、“3·11”地震、福岛核泄漏到伊藤诗织的性侵案,外界能看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压抑的转移”。日本各级政府像踢皮球一样将各式各样的舆论谴责层层向下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体系的平衡。受害人所追求的责任追究和法律诉求就结果而言,最终成为了一种“和稀泥”的状态。
在最近的新书活动中,作家刘柠指出,日本社会正在经历着“国民自主去政治化”的倾向。作为选举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每次选举的时候,投票率却是越来越低,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比例,少之又少。普通人对于政策漠不关心,他们认为那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所以自己的想法不重要。日本社会的政治冷漠似乎助长了统治者逃避责任的心态。
理查德·帕里也在大川小学的悲剧中发现了这些顺从、压抑、沉默的大多数。在他们看来,想要维护和谐,避免冲突,保持沉默是一个关键的要素。人们非常担心,如果站起来抗争,其他人会如何看待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坚忍品性,掩盖了日本人深刻的保守主义内核,身处其中的受害者早已将这种根深蒂固的压抑视为理所当然。作为单独的个体,灾难中的幸存者不计个人得失,勇于自我牺牲,以最大的努力改善现状。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个体的热情和同情心就被维护集体的本能所扼杀,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让这个集体蒙羞。
书中记录了一个片段,有一位遇难者的母亲向作者哭诉。她说,自己的孩子是被一个看不见的“怪物”谋杀了。“我们向它发泄愤怒,可是它没有任何反应。它就好像一团黑影,没有人类的温暖。”她继续说,“海啸是个看得见的怪物。可是,看不见的怪物将永远存在。”作者不禁问道:“看不见的怪物是什么?”“我自己也想知道它是什么,”这位母亲答道,“它是只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独有的,隐藏在那些绝不会说对不起的人的骄傲中。”
记者:李永博
编辑:徐伟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