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非洲本土人文社科传统普遍缺乏了解,在学术引述中大量引用西方学者和不多的中国学者研究,而对非洲本土学者的学术成果充耳不闻。对需要兼顾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的学术研究规范而言,缺乏对非洲人文社科界的领军学者、代表性学说和实证研究的了解,这样的非洲学术研究无疑带有极大的片面性、盲目性,甚至文化中心主义。正如学者景军教授所言,“一个西方学者,来到中国,研究中国农村不关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福建宗族不参考林耀华的《金翼》,研究傣族信仰体系不阅读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研究云南民族医学不对话许烺光的《驱逐捣蛋者》,那么其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盲动。推己及人,中国学者研究非洲社会亦然。”
基于中国学界非洲研究的现状,2019年12月13日,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召集从事非洲研究的中国学者共聚清华园,由社会学系景军教授主持并深入探讨非洲本土人文社科的历史与现状,即非洲本土人文社科的历史与现状会议(第一期中国学者讨论会)。参会学者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德国汉堡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研究国别涉及肯尼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利亚、博茨瓦纳、南非、埃塞尔比亚、马达加斯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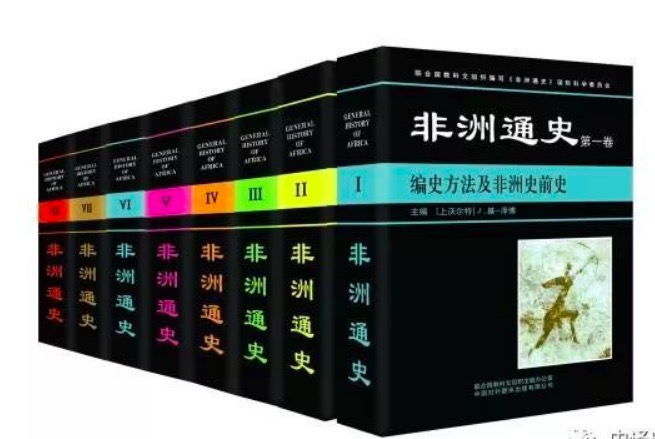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洲通史》
作为非洲研究的先驱,北京大学的李安山教授介绍了其参与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洲通史》的编纂工作。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洲通史》项目是一个长时段工程,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非洲通史》于20世纪60年代推出;第二阶段《非洲通史》的教学使用于2009年推出;第三阶段《非洲通史 9-11卷》于2013年推出。《非洲通史》与以往的非洲历史讲述不同,具有鲜明的本土意识,其编纂目标就是从非洲的角度书写非洲的历史。在1-8卷编纂过程中,约350名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参与,2/3是非洲人,且8卷主编全由非洲学者担任。《非洲通史》向以往的“殖民知识体系”提出挑战,从非洲学者内部视角观察非洲历史,重建非洲史学。应非洲联盟的请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启动《非洲通史》教学项目,向所有非洲大陆学校系统的历史课程插入《非洲通史》的史料。此举旨在教化非洲人及其后裔,构建共同心理框架,反对狭隘的殖民民族历史。
2013年,《非洲通史 9卷》在非洲联盟的主持下初步形成。同年11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任命的16名成员(8名非洲学者和来自欧洲、亚洲、美国、加拿大、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8名学者)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议定项目议程,推动编纂工作开展。与主体而言,《非洲通史》的编纂工作本质上就是批判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从非洲人的角度撰写非洲人的历史,发出本土之声。德国汉堡大学的沈玉宁博士对《非洲通史》的“本土之声”持保留意见,并提出疑问:参与编纂《非洲通史》的非洲学者在哪儿接受的学术训练,是不是西方?《非洲通史》编纂过程中,尽管非洲学者数量居多且担任主编,但是很多通史工作是在西方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本土之声”是否被稀释?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潘华琼副教授详细介绍了塞内加尔和马里的研究机构、学术刊物、领军学者、手稿等材料。
塞内加尔的学术机构,主要有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理事会CODESRIA、达喀尔大学、法国黑非洲研究院。潘华琼重点讲述了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理事会的前世今生,该机构设立的宗旨是通过本土信息收集和研究,推动全非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泛非主义气息,空间有限,经费自筹,机构发展受阻。1978年后,瑞典和挪威为此机构提供资助,但不参与,资助仅仅为了保证这个长期拥有自主权的机构生存。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理事会常务机构有科学委员会、秘书处、图书馆和出版社,资助青年学者为撰写博士论文而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主题颇广,如气候变化、非洲未来灾难等。哥伦比亚政治学教授Mamdani评价该机构,“许多研究非洲的杰作不一定由此产生,但与该机构有很深的关系。”之后,潘老师介绍了Cheikh Anta Diop(非洲学术界“法老”)、Senghor(诗人、学者、总统)塞内加尔领军学者的生平。
另外,塞内加尔五所大学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等500多人合作编纂《塞内加尔通史》,也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洲通史》外,唯一的非洲国别通史。编纂过程引用了大量口传历史、神话,西方学者对史料颇有微词。可是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如何记录,如何撰写也成为学界亟需讨论的问题。至于马里的研究机构,潘老师介绍了阿赫迈德·巴巴高等教育和伊斯兰研究院、巴马科大学、巴马科人文科学研究院,并重点讲述了阿拉伯手稿。阿赫迈德·巴巴高等教育和伊斯兰研究院搜集、保存、编目中世纪的阿拉伯手稿,约3万多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挪威奥斯陆大学和卑尔根大学、马里国家科学技术中心、廷巴克图政府等合作制定廷巴克图图书馆建设计划暨手稿保存研究计划。计划历时12年,图书馆于2009年落成,手稿于2011年迁入。然而2012年极端主义势力占据廷巴克图致使4200多卷手稿被焚毁,剩余手稿则转移到巴马科。
古人类学和DNA谱系研究都把人类的起源指向东非。
浙师大的徐薇副教授从人类学学科视野,讲述了非洲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非洲人类学区域研究肇始于英法殖民时期。为了殖民统治需要,大量人类学学家前往非洲从事基础研究,并创作出大量关注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民族志。英国在非洲推行“间接统治”殖民政策,为人类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其时,非洲成为了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田野材料的来源和理论的试验场,并孕育出Evans-Pritchard、Meyer Fortes、Max Gluckman等享誉世界人类学家及《努尔人》、《非洲政治制度》等人类学经典著作。与英国“间接统治”不同,法国在西非殖民地推行“直接统治”,直接向殖民地输出文化。在此背景下,法国人类学研究更为强调跨学科性和应用性。德国非洲殖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成果不多,但是其纳粹时期的民族学理论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思想源泉,并与英国人类学一道成为南非人类学研究的两大传统。
美国非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Melville Herskovits的贝宁文化史研究,但1980年代之后美国的非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学界主流。西方人类学家成为非洲文化的代言者,湮没了本土学者的声音。鉴于话语权的鸠占鹊巢,在非洲独立之前,本土精英人物积极学习人类学,为本土文化辩护。肯尼亚、尼日利亚、加纳三大开国总统皆获得人类学硕士或博士学位,而尤为突出的是师从马林诺夫斯基的乔莫·肯雅塔,其完成的Facing Mount Kenya成为第一部非洲本土学者的民族志。独立之后,人类学研究因过分强调各部落间文化的差异,被非洲精英视作殖民威胁,阻碍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1970年代之后,人类学的地位有所改观,非洲本土学者更多强调社会问题(如土著人权运动、民族国家建构、自然资源利用等)和跨学科合作,将人类学视作发展与应用的一个理论和实践工具,而不关注人类学本身的理论建构。正如肯尼亚莫伊大学一位学者所言“我们脱离了欧洲人类学,我们不写所谓的民族志,我们追求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可是,非洲大学的大多数人类学教师从西方获得学位,其研究立足本土经验材料,往往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所以,如何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和田野材料,发出真正的“本土之声”,是非洲人类学面临的难题。
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商队
汉堡大学的沈玉宁博士候选人立足肯尼亚研究,主要讲述了肯尼亚制式学科的现实和历史框架、斯瓦希里语在肯尼亚的发展以及Abdulaziz教授的学术经历。
殖民时期,肯尼亚的教育体系基本受西方影响,政府间接资助的教会学校和直接资助公立学校获得绝对优势。其时,教育资源匮乏,且仅限男生,学校建设过程中实行种族分离,白人学习行政管理、历史和艺术,亚洲人学习商业,非洲人学习农业、瓦匠、木匠等“实用学科”,从而形成职业分离。大学教育短缺,直到独立前夕,肯尼亚境内才有大学校区,起初只有工程专业,稍后加入人文学科。而今,肯尼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制和学科体系。作为官方语言的斯瓦希里语,进入教育体制并非自然而然,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殖民前后,斯瓦希里语是肯尼亚海滨地区绝大多数人的母语,在沿海地区文化辐射范围的部落作为跨部落常用交际用语,在内陆地区作为商业语言使用。一战后,英国接管坦噶尼喀,开始将斯瓦希里语当作非洲语言加以推广;1925-1928年,斯瓦希里语标准化规则制定,“普通话”以桑给巴尔岛方言为基础;1930s-1940s,标准斯瓦希里语开始在制式教育领域出现;1950s-1960s,独立斗争期间,斯瓦希里语被大量使用,并被政治化;1974年,斯瓦希里语成为国语;2010年宪法将斯瓦希里语列为官方语言,且在英语之前。斯瓦希里语在肯尼亚的发展跟一位学者息息相关,那便是Abdulaziz教授。他在文学——姆雅卡(Muyaka)诗歌、语言学(“三语”现象,即英语、本土部落语言、斯瓦希里语)、院系建设及斯瓦希里语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推动斯瓦希里语成为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在肯尼亚的发展进程揭示了,本土知识精英一方面参与宗主国知识系统生产,并自动加入到世界知识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根据本国具体情况,积极推动知识生产的本土化进程。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与社科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候选人熊星翰在马达加斯加从事数年田野调查,详述了该国人文社科研究概况。
19世纪以前,关于马达加斯加风土人情的描述材料多来源于传教士、旅行家和商业代理人的记录。1895-1960年法国殖民时期,法国当局基于统治需要对马达加斯加展开系统性的研究。独立之后,法国对马达加斯加人文社科的研究依旧独树一帜,涉及其他国家很少涉及的领域,如城市人文地理、历史人文独家访谈、影像文学及影视人类学。除法国以外,英国、荷兰、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等国学术界也在加大对马达加斯加的关注和投入,学科主要集中在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主题涉及政治、仪式、身份认同、殖民等。
独立之后,受语言和历史因素影响,马达加斯加本土人文社科研究依旧与法国联系密切,其一流学者大多毕业于法国高校。中生代优秀学者大多前往发达国家任职任教,本土学界老龄化情况比较严重。本土学术机构科研经费和调查能力有限,学术研究过度依靠某些教授学者驱动,虽有一定的学术产出,但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还比较有限。马达加斯加属于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生毕业之后的出路并不乐观,很多硕士和博士毕业之后不得不选择与科研教学无关,如三轮车夫、服务员和售货员等职业。这一境况也影响到本土人文社科研究的选题,即由历史文化研究转向发展研究。
在坦桑尼亚经历两年田野调查,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的高良敏博士,目前是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与社会学系联合培养博士后,分享了坦桑尼亚的人文社科历史与现状。
坦桑尼亚最早的学术机构当属伦敦大学东非分部之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其时伦敦大学东非分部的三所学术机构,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学院专注医学,肯尼亚皇家内罗毕学院专注工程、商业、艺术和科学,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则专注法律。独立之后,艺术、科学、非洲研究、经济、语言、历史、文学、医学、农学等专业及相关院系在此生根,学院也逐步拓展为大学。1967年,《阿鲁沙宣言》出台,对坦桑尼亚本土人文社科的发展产生了深彻影响,并在东部非洲、南部非洲的泛非主义、民族主义、抗殖民主义的兴起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此之前,人文社科领域的非洲学者都处于西方学术研究的支配之下,而《阿鲁沙宣言》之后,尼雷尔总统推动坦桑尼亚走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道路,东非大学解体,国家对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更高的期待,人文社科领域开始为适应社会主义做出变更,课程结构调整,师资队伍本地化,唯物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1985年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剧变,本土学者所支持的意识形态逐渐被边缘化,研究方向发生变更。而今坦桑尼亚拥有27所大学,15所大学学院,形成较为齐全的学科门类,Cheche、MajiMaji、Utafiti Journal、Journal of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in Education、Tanzania Journal of Sociology (TJS)、The African Review等人文社科期刊杂志纷纷出现,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Mkuki na Nyota Publishers Ltd等出版社成立并支持人文社科著作的发表。
一直以来,“重塑历史”是坦桑尼亚人文社科领域发展和变迁的重要方向。1967年,A history of Tanzania编纂完成,虽强调“非洲人自己的历史”,弱化殖民影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西方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依旧占主导,书目的综合性不强,未能体现沿海史与内陆史之间的关系张力。
时隔五十年之后的2017年,A new history of Tanzania编纂完成,与前著不同,虽然仍有外国学者及其成果的零星身影,但本土学者已成为主导;在素材方面,研究注重结合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历史语言学、口述史等学科挖掘材料,呈现更为综合的坦桑尼亚新史。新史的编纂成功得益于非洲本土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创作的Memoirs of an Arabian princess from Zanzibar、Tanzania’s political culture、Tippu Tip、Bushiri、Hadzabe、Human Sacrifice、Mask of the Spring Water、The ways of the tribe等一系列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作品。
除此之外,清华大学的唐晓阳老师以一个乡村博物馆为切入点,以ajobi(基于血脉联系形成的团体,代指尼日利亚的本土传统知识)和ajogbe(没有血脉联系而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团体,代指现代社会)为关键词,解读尼日利亚本土学者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中山大学的陈亮博士基于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的田野作业,讲述如何利用亲属制度、边疆历史(族长、上尉、老人的口述史)、城镇中个体的生活经验(如牧民、商人、官员等)、信仰生活(精灵师、占星师、伊斯兰法官、商人)和习惯法体系等田野材料进行边疆知识生产,发出本土生活之人的心声。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陆继霞教授则从自身的工作出发,讲述了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援助问题,得出“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为政治中立的平行经验转移”的结论。
共识
参会学者均为非洲人文社科研究的先行者,都有长期的非洲田野调查经历。会议过程中,除了分享非洲诸国人文社科研究传统外,非洲研究学者还对目前中国非洲研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一些共识。
1.对人文社科研究而言,非洲拥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往往成为西方学者提炼理论的富矿和西方学术理论的实验场,从而湮没了本土行动者的声音。值得庆幸的是非洲本土学者开始崛起,关注自身社会的问题,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之声”,也就是原创性的理论依旧稀缺。
2.中国非洲研究的意识与西方国家不同,恪守政治中立,且无殖民遗存之影响。中国非洲研究最为注重的新知识的生产,通过对非洲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丰富人类的知识库。其次,中国学者对非洲社会进行跨文化研究,一者对比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之间的差异,反思、质疑、重新认识自我文化中老生常谈的现象,二者了解他者文化的思维习惯,反思、质疑、重新认识自我文化中习以为常的思想。
3.非洲人文社科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生产出经典的人文社科著作。而产出经典著作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为了创造良好的知识积累环境,中国海外研究面临的一系列程序问题需要引进学界,乃至中国社会的关注。这些程序问题包括田野进入问题、伦理审查问题、中非学术机构合作问题等,其中田野进入问题最为基础。田野进入的可行性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学者,而今在非洲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很少拥有调查许可。究其原因,并非中国学者不愿意申请调查许可,而是对象国政府拖沓的行政效率和机构腐败致使调查许可申请过程中横生枝节。与非洲科研机构合作,可能是解决调查许可的可行性方案,然而目前固定的双边合作协议缺失。遍布非洲诸多大学的孔子学院是目前最为成功的中非大学合作模式,但是孔子学院专注于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但并不注重学术研究。如此,整合资源、搭建联系、机构合作应该成为深耕田野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