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写了一篇书评,谈及清末民初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刊《说部丛书》里的翻译底本问题。这有幸引起中国近代小说研究权威、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先生的关注,他在自己的清末小说研究网站上转发了书评的消息,并肯定了我在书评里提到的一个新发现:《一柬缘》的原作就是英伦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小说家夏洛特‧玛丽‧布瑞姆(Charlotte Mary Brame,1836-1884)所写的 Lord Lisle's Daughter(1880)。樽本先生认为,这个发现还可以纠正此前日本学人对菊池幽芳《乳姊妹》 (春阳堂,1904)原作的认识,他们认为这翻译的是布瑞姆夫人的另外一部小说( Dora Thorne,1877),并煞费苦心来弥合原作与译本的差异,做出了很牵强的解释。而熟悉日本翻译文学史的台湾学者继而又以这个线索来解释《一柬缘》的底本,因为《乳姊妹》的内容和《一柬缘》非常近似。现在找到 Lord Lisle's Daughter,再逆推回去,才发现《乳姊妹》和《一柬缘》一样,是这个小说的译本,并且稍晚出现的《一柬缘》是直接从英语译出的,不属于小说《电术奇谈》那样的“英国→日本→中国”的传播方向。
对樽本先生这番见微知著的阐发,我由衷表示感佩。这也再次印证了我的一个想法: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很值得重写,这需要依赖新时代的技术条件和文化视野,而一切的根本就在于对那些尚未了解其翻译渊源的文本逐一清查考证。记得樽本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讲过类似的话,大意是近代文学研究需要现在文献考证的琐细之处下大功夫才能发展。这几天,由于写书评的缘故,我将尚未考出原作的《说部丛书》部分又翻出来看了看。2017年夏天,我新查考出其中翻译原作二十种;2019年,樽本先生又公布了比如《重臣倾国记》《美人磁》《铁锚手》《海外拾遗》原作的考订结论;现在对照近日才发布的樽本先生《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十二版 (下文简称樽本《目录》),略下了一点功夫,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其中二集第七十五编《错中错》,崔文东兄在我之前已考出原作,他在写一篇专门的论文,我不能掠人之美。而以往的考证过程中,都免不了通过对作者译名、人物译名乃至主要情节的判断,去翻检有关工具书,包括作家名录(比如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Authors和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Writers, 19th Century等书)、文学人物名录(比如 Character Sketches of Romance, Fiction, and the Drama和 Dictionary Of Fictional Characters等书)以及类型小说题名录或是描述性的叙录(比如那部著名的 Science Fiction: The Early Years, A Full Description,这才是小说文献“叙录”该有的样子)——这些方法,在此野人献曝,愿意广泛传播、分享给各位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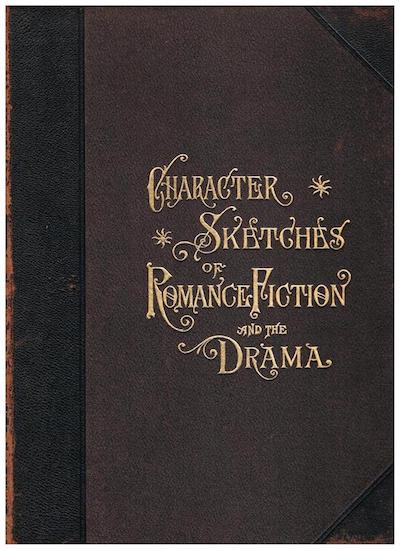
Character Sketches of Romance, Fiction, and the Drama
Science Fiction: The Early Years, A Full Description
然而值得分享的又不仅是考证的小结果或是某种方法。在积少成多的过程中,我开始感到收获更大的乐趣,是在于量变积累下跃升出的一种观念认识上的变化。我觉得深入的阅读和考证或多或少地在改变着既有文学史、翻译史观念的框架和表述。我希望在介绍以下新发现的同时,也尽力兼顾对这种改变的感想。
(一)二集第七十七编,《堕泪碑》。题署“(英)布斯俾著,商务印书馆编”。
学界早就断定作者为作品在清末民初译介甚多的盖伊·内维尔·布思比(Guy Newell Boothby,1867-1905),然而并未进一步查考原作。《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莫名其妙地指认同集第二十九编的林译小说《女师饮剑记》原作为此书,这可能是抄袭了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的说法。樽本《目录》已明确指出,《女师饮剑记》原作是布思比的另一部小说 A Brighton Tragedy(1905)。
我这次逐一查对网上可看到的布思比作品,终于找到原作即 Love Made Manifest(1899)。布思比是长期生活在英国的澳大利亚籍小说家,长于“哀情小说”,吉卜林和奥威尔都受其影响。这部《以爱为证》在今天似乎不像这位作家的“尼库拉”系列那么受欢迎,但对认知布思比本人思想颇为重要:小说主人公“可洛”(Claude)年轻而又充满斗志的形象就是他本人的写照。开篇有一段话就是自叙心曲:
澳大利亚洲为一商场繁盛之域,文物荟萃之邦,凡属有用人材,本足以消容而有余者,惟可洛蛰居久之,仍郁郁不得志。
(The Colonies, ever ready to claim talent when it has been thoroughly recognised elsewhere, were almost stoical in their firmness not to encourage his life as an usher in a small up-country to any living child of man.)
对照原文,虽然有些走样,但大体描绘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生长于殖民地的大英帝国新世代人心灵轮廓,其中积蓄了作者本人航海旅行四处游历的全部动力,也成为他后半生写作大量小说的起点。从这一点上看,清末翻译史对英国近世文教风化的理解是颇为贴近的,我们不应该总是从文学史所框定的重要作家作品的范围来估衡这些译作的价值。
《堕泪碑》原作
《堕泪碑》原作插图
《堕泪碑》封面
(二)初集第七十九编,《金丝发》。“侦探小说”,题署作者为英国“格离痕”。
事有凑巧,正好我最近在iPad上翻看了几部早期女侦探小说家研究著作,并且按图索骥收了一部Delphi Classics在2017年制作的《安娜·凯瑟琳·格林全集》( Complete Works of Anna Katharine Green,epub格式电子书),因此这回从译名“格离痕”的发音马上就产生联想,锁定范围,发现主人公“克利司”正是这位格林女士创造的名侦探,人称“格莱斯先生”(Mr. Gryce)。《金丝发》的原作就是“格莱斯先生探案系列”的第二部,《失踪奇案》( A Strange Disappearance,1879);而此书开篇虚设人物面对作者所说的“君所著之勒芬浮斯案”,就是特别著名的《利芬沃思案》( Leavenworth Case,1878),此书近几年至少出过两个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把这位作者的国籍也搞错了,格林女士(1846-1935)是美国第一位写侦探小说的女作家,被誉为“侦探小说之母”。她比阿加莎·克里斯蒂、派翠西亚·温渥斯更早发明业余妇女破案的小说写法,开启女性如何利用自身的智慧与感觉来抵抗社会黑暗面的文学主题,而《金丝发》正被认为是格林借由一起家庭暴力案件控诉女性被任意伤害的代表之作。
《金丝发》原作首页书影
《金丝发》封面
研究十九世纪女侦探小说家的著作封面
(三)初集第七十一编,《圆室案》。“侦探小说”,作者是英国的“葛雷”,与《金丝发》一样,译者都是“编译所”。
开篇提到“美国侦探格莱史”,我由《金丝发》原作的水落石出而得到启发,顿时明白,这部小说也是美国作家安娜·凯瑟琳·格林“格莱斯先生探案系列”里的作品。逐一排查,发现原作即《圆室探究》( The Circular Study,1900),为系列里的第十部。
如同首部曲《利芬沃思案》一样,《圆室案》处理的也是一起密室杀人案件。小说里再次出现了房屋的构造平面示意插图。“密室杀人案件”是侦探小说里最有吸引力的一种设计方案,因为是近乎不可能的犯罪,所以最考验侦探本事。从相当于外国“豆瓣网”的“Good Reads”此书页面的热烈讨论所见,侦探迷对这部小说的兴趣至今不绝。这部中译本在1907年问世后应该也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写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攻击“古文译书”,除了再次奚落林纾的“其女珠,其母下之”,临时拉来陪绑的就是这部小说:
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
“拂袖而起”出现在小说的第一页,原文是“格莱史大惊,拂袖而起”。看起来胡适是没有打算翻阅下去的兴趣,他只比今天某些研究近代翻译小说而只看序跋和版权页的专家好一点,多读了第一页而已。假如我们拿“拂袖而起”“拂袖而去”这个说法在现代文学作品检索一下,就会发现很多语例,甚至见于鲁迅的《两地书》。因此,若是仅凭借这样一个用词就否定说“不如不译”,实在过于武断。唯一合理的解释,还是《说部丛书》这些小说在当时大有市场,新文学阵营不得不摆开架势来争夺合法身份吧。
《圆室案》原作书影
《圆室案》书影
(四至六)三集第七十四编,《白羽记初编》;三集第八十三编,《白羽记续编》;三集第九十六编,《白羽记三编》。未标原作者,译者沈步洲。
这套《白羽记》是《说部丛书》里来历不明的篇幅最大一部小说,分成三编六册译成,总计约四百二十多页。沈步洲有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的经历,编写过英语文法书,自然有比较好的文学素养,文言译笔如此详尽,说明对原作非常重视。因此,我将考证此书原作视为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工作。
经过若干琐细繁忙又白费工夫的猜想和排查,终于发现原作就是英国作家阿尔弗雷德·爱德华·伍德利·麦森(Alfred Edward Woodley Mason,或作A. E. W. Mason,1865-1948)的传世名著《四根羽毛》( The Four Feathers,1902)。这部小说被七次改编为电影,在网上还可找到一部活动木偶影片。最近拍的一部电影是2002年上映的,国内观众非常多。小说讲述一个被同袍和未婚妻鄙夷为逃兵的英国贵族军官,在愧疚和自责下悄悄奔赴苏丹前线,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乔装成阿拉伯人拯救了朋友们的生命。“白羽”是小说里的一个主线,这是怯懦的象征。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背景里的战争,对应的乃是1884年的苏丹马赫迪起义:英属殖民地的人民发起暴动,抵抗英军与埃及军的镇压。时任苏丹总督的查理·乔治·戈登,也就是当年协助李鸿章打击太平天国军队的洋枪队头目,被苏丹起义军围困于喀土穆城。英政府派军队前去解围未能成功,反而损失惨重。因此,主人公起初在大婚之际接到奔赴前线的命令,拒绝履行军人的义务,看似是以个人意愿对抗民族大义,其实则可看作帝国繁盛时代的个体精神反思殖民地战争的道义价值。他以个人情感为重,深入死地拯救友人,则又进一步让帝国战争分子的狂热情绪和傲慢心理在人间友爱的私德光芒下显得无比卑劣。
这部《白羽记》虽然也以文言译出,但译笔非常细致,并且沈步洲极为尊重原作的细节,用详尽丰富的译注来尽力还原这一小说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此外,麦森还以侦探小说名世,他创造的“哈诺德探长”(Inspector Hanaud)启发了“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罗”形象。而“哈诺德”系列中的 At the Villa Rose(1910),就是樽本先生从前考证的周瘦鹃译《毕竟是谁》 (《小说时报》1915-1916年连载)的原作。
《白羽记》原作书影
《白羽记三编》封面
《白羽记续编》书影
《四根羽毛》原作改编电影海报,发行年份(从左至右、由上到下)分别为:1915、1929、1939、1978、1955(更名为《尼罗河风暴》)、2002
(七)初集第九十编,《一仇三怨》。“婚事小说”,题署美国“沙斯惠夫人”著,“编译所”译。
我将查考的线索首先放在比较完整又独特的作者名上,对照相关的美国女小说家名录,马上注意到有一位叫索思沃司(Emma Dorothy Eliza Nevitte Southworth,1819-1899)的女士,但她写的长篇小说太多了,大约有六十多部,而且风格大体相近。就在我翻看到几乎头晕眼花想要放弃的时候,才找到一部题为《失踪的新娘》( The Missing Bride; or, Miriam, the Avenger,1855)。中译本对原作第一章仅译了开头两三句,即接第二章内容,略去了有关主人公祖先发家史的冗长记录。这位“沙斯惠夫人”刻画女性人物,重其针锋相对的机智、铤而走险的勇气以及不畏命运的叛逆精神,与英式维多利亚文学里的家庭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因此,中译者也许在具体选择上没有注意到应该翻译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但在对小说价值取向的判断上应该说还是很有想法的。
《一仇三怨》原作书影
《一仇三怨》书影
(八)二集第八十九编,《飞将军》。“理想小说”,署“葛丽裴史原著,天游译述”。
此前,古二德(César Guarde)先生在《清末小説から》121号有一篇文章《〈毒美人〉等原著鉴定及〈东方杂志〉佚名译者身份研究》,其中提到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在1911年至1912年连载的一部“白话理想小说”《新飞艇》,署“葛丽斐史”,这就是单行本《飞将军》 (1913年6月初版)此前的杂志连载文本。这次从“葛丽斐史”这个名称下手,也就好办了。我在一部简目工具书( The Checklist of Fantastic Literature, a Bibliography of Fantasy, Weird, & Science Fiction Books,1948)里查到了名字发音最接近的一位男性作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家乔治·格里菲斯(George Griffith,1857-1906)。《飞将军》翻译的乃是他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作品,《革命时代的天使》( The Angel of the Revolution: A Tale of the Coming Terror,1893)。小说将技术革命的想象与俄国社会革命的热潮联系起来,预言了尚未到来的新世纪种种灾难与希望。
《飞将军》原作
《飞将军》原作插图
《东方杂志》八卷全年连载的《新飞艇》(即单行本《飞将军》)
(九)初集第九十一编,《新飞艇》。科学小说。
上述古二德文章中还提到了与《飞将军》连载本题名相同的这部小说,但显然不是一部书。此《新飞艇》的主人公是“纽约名侦探尼楷脱”,其实就是清末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聂格卡脱侦探案”系列的主人公,尼克·卡特(Nick Carter),这个形象是1886年出现在《纽约周刊》上的一个小说人物,后来经众多作家续写其侦探故事,流行了一个多世纪。
这部《新飞艇》同很多《说部丛书》乃至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作品一样,出自英美廉价畅销文学书刊所谓“一毛钱小说”(dime novel)的代表。现在各种国内研究清末小说的书目,都引述《新飞艇》版权页的“尾楷忒星期报社著”,樽本《目录》已经指出“尾”字乃“尼”字误植。“尼楷忒星期报社”,指的就是尼克·卡特这个人物形象在美国走红后出现的一种专门的小说杂志,《尼克·卡特周刊》( Nick Carter Weekly),从1897年第一期到1915年停刊(此后更名为《侦探故事杂志》,1920年又继续刊登“尼克·卡特”系列),大约出了九百期以上,在网上看到有收藏者把这个杂志收到八百期的。
我费了一些时间,把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廉价小说”(Nickles and Dimes)网站所上传的大约七百多期《周刊》开篇翻了一遍。发现《新飞艇》的原作即1907年3月16日的《新尼克·卡特周刊》,这是第五百三十三期,题为《直面看不见的恐怖》(Facing an Unseen Terror, or, Nick Carter's Day of Blunders)。我发现找到原作这个工作,不仅是在确定考索范围后因数量仍然庞大而难解,中译者(署名“编译所”)还在叙事顺序上做了很多简化调整,除了很少量的几个明确信息可以在对照中呈现出来外,很难一眼就认出译本和原作文本的联系。
推究原因,我觉得译者可能也并不重视这种小说作品,同时也多少存有刻意减少叙事风格上的异域陌生感,这在《说部丛书》内部来看,与那些严肃小说的翻译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分野。此外,《说部丛书》二集里还有两种汪德袆译作,分别是第四十六编的《假跛人》和第八十五编的《秘密室》,主人公也都是尼楷脱,但我在所见的七百多期《周刊》中还没有找到明显与这两部相对应的原作。此外,二集八十二编《城中鬼蜮记》也是汪德袆译述,此前已考出其原作也是一部文学价值不高的小说。
《新飞艇》原作封面
《聂格卡脱侦探案》书影
《新飞艇》原作首页书影
《新飞艇》首页书影
除了以上有明确“实锤”的发现,还有两个线索出来了但囿于网络资源有限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作品。在此记述如下,以供同好参考。
(一)三集第九十五编,《红鸳艳牒》(陈大悲编译)。
此篇作品在1918年初的《小说月报》第九卷一至二号连载时,作者署为“J. U. Gieiy”,后来学者又误改为“J. U. Giety”,其实应该是指约翰·乌尔利奇·基西(John Ulrich Giesy,1877-1948)。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基西是我挺感兴趣的一位科幻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是在1918年之后在通俗小说杂志上连载的保罗斯三部曲(Palos Series),这属于“剑与行星”(Sword and Planet)类型小说(即电影《异星战场》那种风格),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蒸汽朋克”风不太一样。然而《红鸳艳牒》显然翻译的是一部并不出名的作品,以致于可能只存在于当时的某个杂志上,即便是科幻迷也顶多收其题名,令我无从查对。
刊载约翰·乌尔利奇·基西代表作的通俗小说杂志封面
《红鸳艳牒》封面
(二)初集第四十四编,《红柳娃》。“探险小说”。题署美国“柏拉蒙”著。
书前有“译者按”,言“取向有‘红柳娃’之名以名之。至于初译数纸,予当时易去原书‘黑暗里面之真相’旧名,而名以‘蓬艾怪谈’”云云。在樽本《目录》里可以查到,1904年3月《警钟日报》上曾经连载过一部《蓬艾怪谈》,署名是“美国柏拉蒙著,震旦无竞生译”。连载未完成即中断,随后在《警钟日报》1904年3月25日有则启事,言“本报前几号所载之《蓬艾怪谈》乃译和文谷川澄一所著《黑暗里面之真相》。现仅登录半卷,译者为他事稽延,略停十数日即可复译登出”。这与前面所引那段“译者按”说的非常吻合。若找到当时的谷川澄一日文译本,应该就能水落石出。但我也不熟悉当时的日文翻译情况,也就止步于此了。
至此,《说部丛书》的三百二十种左右小说,未明来源所本的还有五十种左右,我感觉几乎都是不好解决的了。以上多啰嗦几句,对自己怎么发现线索顺藤摸瓜去查考原作做了些说明,为的是可以减省他人重复不必要的摸索,更重要的也是提供一个方法上的批判对象,敬请更为高明的方家赐教指正。但是话说回来,这番捕风捉影的“考证”过程,也不是全无价值的。通过对若干名不见经传的外国小说作品的广泛接触,我觉得更能贴近去体会清末民初中国所处的世界文学氛围,尤其是清末民初对西方同时期流行小说的认识,从那些虽然不甚高明却妇孺皆知的故事中,逐渐体会现代小说如何使用叙事、对话和心理描写,观察人性的欲望与罪恶,注视故事中的自然风景、人间幻梦、历史环境、社会万象乃至未来图景。
我们今天对《说部丛书》里还有这么多小说难以考实其底本,恰恰也说明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很多文学热点,我们的敏感度和关注度都是不及当时的了。这个问题在大浪淘沙的文学史观念照拂下,固然可以不屑一顾,然而在我看来,假如改从比如阅读史、书籍史、新文化史这样的研究视野重新打量,那种仅以文学史重要作家为核心的文学交流研究模式总还是显得有些空洞乏力的。新材料、新发现不断出现,如何另辟蹊径,才是更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