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认识分析传统与欧陆传统
接上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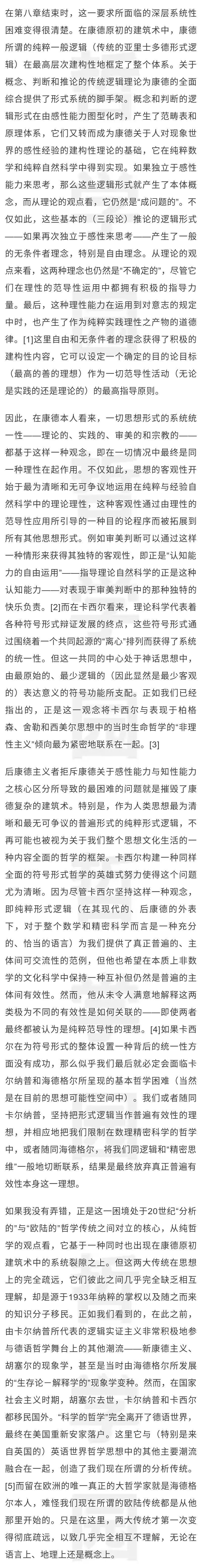
[1] 这一过程也包含着表达知性能力之本性的概念和判断形式。 因为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题为“论纯粹实践判断力的范型”一章中所解释的,实践理性这里并不运用于感性能力,而是运用于知性的一般形式本身。 由后者产生了一个由定律支配的自然体系的一般观念,它又成为对绝对律令的所谓“自然定律”表述之基础。
[2] 这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中对审美判断的普遍可传达性的解释的关键点。
[3] 卡西尔当然很清楚他这里所走道路的微妙性和不稳定性。 比较第八章的注释182。 然而,正如我在第八章的其余部分所要表明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似乎并没有系统性的资源来将这条道路成功走到底。
[4] 参见注释192和193及其所对应的文本。
[5] 由于1945年过早去世,卡西尔从未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分析传统的一份子。 他仍然继续按照我们今天所谓的欧陆哲学家的风格和主旨进行思考。
[6] 前一类型的哲学家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弗雷格,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持有强烈的反民主甚至是反犹的政治观点。 他与他的朋友鲍赫持有不少相同的观点,后者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成为“纳粹哲学”的一位领袖(与鲍赫相比,海德格尔本人与纳粹的牵连有些黯然失色)。 关于对弗雷格和鲍赫的讨论,参见[Sluga, 1993] (关于鲍赫早期对柯亨的康德解释的反犹主义攻击,亦参见 [Krois, 2000],它预示了施潘在1929年的攻击: 比较前面注释7)。 海德格尔的“进步”(或者至少是左派)学生和追随者的重要例子当然是马尔库塞、阿伦特和萨特。
[7] 在这方面,卡尔纳普对“新的客观性”的认同远比纽拉特彻底。 与卡尔纳普不同,纽拉特无意将哲学本身转变为一种“客观的”(纯技术的)学科。 参见前面注释20中所引用的对纽拉特的评论(以及它所对应的文本),并且比较[Carnap, 1963a, pp. 51–52]。 关于纽拉特本人的观点,再次参见前面注释19中所引用的文献。 在关于维也纳小组与“新的客观性”之间关系的非常有用的讨论中[Galison, 1990],卡尔纳普与纽拉特之间的这一重大区别似乎被遗漏了,它总体而言忽视了两位哲学家之间分歧的重要方面。
[8] 在由卡尔•洛维特所报导的一次著名对话中(1936年)[Wolin, 1991, p. 142],海德格尔完全清楚他的政治牵连和他对必然的“此在的历史性”的哲学观念之间的这种关联。 奇怪的是,这一重要关联在对海德格尔哲学与德国新保守主义之间关系的非常有趣的研究[Bourdieu, 1988]中似乎被遗漏了。
[9] 再次参见 [Krois, 1987, chapter 4]。
[10] 正如我们在注释10中所指出的,在卡西尔身后发表的《国家的神话》中,他与此走得最近。 尽管有一些缺陷,但这部著作包含了对现代政治的法西斯主义权力的一种非常敏锐和中肯的诊断,根据卡西尔的说法,法西斯主义在于它有意地以现代技术(大众媒体)为工具来操纵更加原始的神话的思想形式。 关于对这部著作的优缺点的比较公允的讨论,参见[Krois, 1987, chapter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