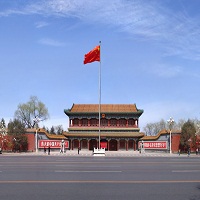姚敬舜:沧海桑田两甲子,复兴华章看今朝—— 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好书推荐

2020年是农历庚子年,这一年的春天虽姗姗来迟,但依旧朝气蓬勃。这一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千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剧震,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从未像今天这样坚定而有力。如果将时光倒带两甲子,1900年的庚子年则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中国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中沦为俎上鱼肉,每个中国人也耻辱地背负上了一两白银的强权负债。其实再往前推一个庚子年,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曾为救亡图存做出努力尝试,甚至开创了同治中兴这个昙花一现的盛况。古今多少事,并不能尽付笑谈中,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近代有识之士的挣扎、探索和局限,都将为我们在船到中流浪更急时深化改革开放,在黑天鹅频频的国际大变局中涉险滩、勇开拓提供宝贵的镜鉴。
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中,美国著名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记录了清政府的有识之士在面临太平天国割据东南半壁、列强借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帝国政治和经济秩序到了崩溃边缘的局面下,力挽狂澜重整国家秩序的奋斗过程。但即使清政府将传统社会的张力和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仍然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大潮抛弃,中兴成果付诸东流。简而言之,同治中兴是清政府将全新的时代挑战错认为中国历史的盛衰循环周期,单纯依赖传统力量来抵御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徒劳尝试。因此,同治中兴是抗拒现代性的失败,是抗拒解放思想的失败,也是抗拒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失败。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同治中兴之败,首先单纯依赖礼制和人制之败。自始至终,清政府对于社会治理的全部努力仅仅局限于重新规范社会等级体系和每个人的权利义务。清政府试图借此革除社会运行中的磕磕绊绊,回归传统和纯粹的礼教旧秩序。但这一体系只能依赖道德和说服发挥作用,法律框架和制度建设的缺失,导致清政府失去了在政局混乱、礼崩乐坏的危机时刻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此外,在礼制框架下,官僚最主要的施政训练、工具和评估体系都围绕道德教化展开,这就极大阻碍了官僚系统的人员分工和专业化,而处理具体事务的权力就此落入胥吏之手,后者不受礼教束缚而恣意妄为,制造了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反过来危害了礼教秩序。而国外人才与传统礼教的高度不相容性,导致了清政府即使在打开国门后,也无法集天下众智为己所用的窘境。最为可惜的是,缺乏制度的可持续支撑和规范,中兴的成败仅仅依赖中央和地方数个名臣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当中兴名臣相继凋零,同治中兴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清王朝衰亡之路上一个悲剧的历史注脚。
发展是硬道理。
同治中兴之败,是存量思维之败。同治中兴时期,清政府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经济发展附属于政治秩序的阶段,因此一以贯之的经济思想仍是重农抑商。在清政府强调循环而非发展的世界观中,经济政策的目标从未超越恢复王朝元气、重执东亚牛耳的限度,这在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时期或许有效;但是当世界已经拉响了全球化的汽笛,在一日千里的工业革命浪潮中,激烈而残酷的国际竞争已经将各国已经逼到了不进则退、不进则亡的生死攸关境地。清政府将维持财政稳定的希望寄托于小农经济及节约开支之上,因此彻底失去了通过现代贸易和金融扩展发展空间,乃至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争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此外,国际博弈就是争取最多的朋友,对抗最少的敌人。尤其在重商主义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贸易更是缓解国际冲突不可或缺的镇定剂和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催化剂。清政府对贸易的无视与限制,不仅失去通过拉拢英法以有效遏制沙俄对华领土野心的机遇;也大大激化了欧美商业利益集团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及侵略意识,成为后期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的一大诱因。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同治中兴之败,更根本的在于固守僵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之败。儒家思想在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恢复国内秩序的过程中承担了弥合满汉民族矛盾、搭建政府和士绅价值同盟的意识形态支柱作用。但当清政府的领导者们掀开中兴的新篇章,其手段和目标却仍离不开君臣父子、忠孝仁义的儒家旧框架。在短暂达成传统意义的社会稳态后,清政府领导者们迅速失去了探索国家认同和发展伦理的动力,逐渐陷入了“稳定陷阱”。这种在多元化时代下执念于单一手段、单一目标的选择,导致清政府在推动最有限的技术革新时也步履维艰:在士绅和传统官僚阶层的敌视和掣肘下,新生的近代工业沦为清政府的财政黑洞;而同文馆编译的文献更多束之高阁。更为可惜的是,清政府大力维护的儒学思想并没有培育出社会各阶层的国家认同和集体救亡意识:士绅深情论述和捍卫的更多是儒家这一文化或生活方式,而非国家本身。这也难免当甲午战争爆发时,外媒发出了“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的感慨。而儒家思想在过度保护下逐渐失去理论韧性和时代内涵,也酿成了20世纪初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全盘抛弃传统价值的悲剧。
这本书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一经出版就成为西方研究近代中国的经典之作。作者在观察了清政府、袁世凯政权、蒋介石政府一系列的失败后,得出了“不存在把一个有效的近代国家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的途径”的结论。但当我们拉长时间的维度,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让我们完全可以具备更有力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与时俱进的儒家文化是一股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和精神力量,可以与现代治理体系和发展模式形成最佳的匹配融合。儒家凝聚社会认同和强调公共责任的天然力量,以及对良治和善政的强大鞭策作用,融合现代市场经济商业伦理,将形成激发社会全要素潜力的最大合力。近期面对疫情,中国从传统基建狂魔、到新兴互联网的各行各业力量纷纷快速响应,最大程度和最高效率地参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治理就是一个明证。社会全要素的有序组织和广泛参与,促进了相互间的互联互通、形成了进一步改善社会治理的合力,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国家和社会认同,为在全新的庚子年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持久和稳健的精神动力。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世界,自殖民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其他文明形态的接受程度,一直取决于这些文明对西方政令、制度和价值观的服从程度。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只在它扎根的土地上一脉相承地发展,与环境和历史形成统一的和谐整体,并不存在全盘移植和复制文化的可能。对于中国的独特性缺乏理解和包容,造成了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乃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误解、曲解甚至恐惧。当下全世界的抗疫之战不光是一场与病毒的战争,更是一场对各国体制的大考,一场基于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秩序洗牌。在改革开放中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体制,让我们在歼灭战、持久战、总体战中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执行效率,赢得了举世的关注和认可;而根植于儒家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将通过中国在抗疫之战中与世界各国的守望相助,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有力的东方智慧支撑。
从更宽广的维度讲,全球化的时代带来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利好,也带来了跨越边境的国际挑战,任何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单个民族国家的资源和国力也渐渐无力应对。或许超大型政治经济共同体将为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提供一个潜在解决方案,而中国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模式也可能为这一现代危机的解决之道提供一定启发。
丘吉尔说:永远不要浪费一个好的危机。同治中兴错失了救亡图存的机会,致使20世纪初庚子年留给中国的,是无尽的屈辱和痛苦。而在21世纪这个全新的庚子年,在经历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后,我们可能不会再回到熟悉的昨日生活,但是通过40余年传统价值和现代文明的不断磨合蓄力,我们的社会肌体将更加强健,我们的价值共同体将更富生机,我们也将带着更大的自信为世界文明秩序注入更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