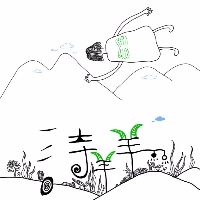阿姆斯特丹
——在凡高的呼吸中
荷兰有些焦虑,十九世纪荷兰最骄傲的儿子凡高的画他们收藏得不多,伟大的杰作散佚在世界各地,凡高是属于全世界的。但荷兰要证明他是她的儿子,所以在1973年建立了凡高博物馆。又用很多的钱到世界上收买凡高的画,但许多杰作是难以买回来的。在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共有凡高的200多幅油画,500多张素描。
我去的时候是秋天,阿姆斯特丹下着细雨,但不冷。从红色的火车站出来,随便问一位老太太,她仔细辨别了我的朋友用蹩脚的英语发出的VanGogh这个名字的发音后,忽然间做出恍然大悟状,指点我们去乘5路电车。凡高在荷兰是无所不在的,不仅书店,甚至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都可以买到29盾一套的凡高全集。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停车场,以为里面在办展览,进去看,一个人也没有,凡高的画被一幅幅用颜料喷了个大感觉在墙壁上。到达博物馆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门口还在排着长队,天天如此。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除了火车站左边圣.尼科拉斯教堂后面的红灯区,恐怕就是这个博物馆了。一个通向地狱,一个朝向天堂。这是人类的两极,也是阿姆斯特丹的魅力。在这个上帝已死的年代,真正能够让人灵魂出窍的人物,恐怕就是诗人和艺术家了,他们是人群中的先知。像上帝一样,总是上了十字架,人们才发现,上帝就住在我们隔壁。当年,集体写请愿书把凡高,一个令人讨厌的穷鬼兼疯子送进精神病院去的,正是他的邻居们。
博物馆的布局很有想法,二楼是凡高的原作,一楼和三楼的馆则收藏凡高同时代画家的作品,让人可以看出凡高画什么,他同时代的人又在画什么。我在1981年就看过凡高的原作,是哈默带来北京展览的藏画,我记得是凡高的《圣雷米医院》。凡高也许是在中国被人们谈论得多的西方画家,他像烈士一样的被谈论,向日葵、星夜、咖啡馆和麦地上的一枪。
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也许是中国卖得最多的画家传记之一。凡高,烈士、大师和悲剧的一生。我想起我在大学时代,谈论着从凡高的传记里看来的轶事,抱着吉他(弹得很差)留着长发,喝着酒,想象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怎样?与妓女睡觉,?疯狂?没有钱,割掉耳朵,在法国阿尔的烈日下,被太阳晒得皮肤焦黑?用枪朝胸口上轰一下,倒在麦地里?凡高死的时候可不是作为大师,而是和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他的原作证实,他长的是一副留短发、穿西装的其貌不扬的庸人相貌。
世界永远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或浪漫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成功的天才。升华与遮蔽,如此而已。据说他是为代替人类受苦受难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但人们进入凡高博物馆的时候,有时却带着看这些葵瓜子怎么会值一百万美元这种心情。我听到同去的中国诗人在凡高画的靴子面前,指点着,说,这就是海德格尔评论过的那一双啊。指着《麦田里的鸦群》说,这是杰作啊,非常有名的呢。我赶紧关掉耳朵,走开了。
我怎么能在这些作品面前出声。我距它们只有一肘的距离,我听得见凡高在劳动时的呼吸。
在二楼有一个十米长的橱窗,里面展览的是凡高早期的作品。我看到,从未读过美术学院的凡高,对绘画的那些不代表什么主义的基本技法——素描、写生、石膏雕塑等有很深的功夫。他做的三匹石膏的马,相当真实、老实。想起在昆明,美院的老师教一年级的学生搞什么表现主义,使许多学生以为创造一种主义比画一张素描更容易,也更是“艺术的”。如果我告诉他们,凡高其实不过是老老实实的画画,发现了自己的方法而已,他们肯定以为我扯谎。凡高,一个苦难的灵魂,灵魂!他们大声抗议道。
在这个博物馆里,不出名的作品很多,许多是凡高早期的作品,他的代表作在这里不多。这是艺术史的看法。但我自己有我的眼睛啊!我现在不是看印刷品,而是面对原作。我的眼睛呢?我们是否能够像1888年10月高更在阿尔的凡高的画室内那样看这些油画,我面对的是原作还是艺术史?是那个耳朵上缠着绷带的凡高,还是博物馆印在凡高画册封面上的凡高?如果我面对的是艺术史,我又何必到阿姆斯特丹来,中国有的是凡高的印刷品。
我后来在巴黎也看到凡高的杰作,举世闻名的几幅,挂在艺术史的某一页上。它们仅仅是一些艺术史的抽样标本,为某个批评家的高论作做做注脚而已。印象深刻的还是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这才是凡高的家。据说这里是由提奥的后人在管理。
早期的色彩是阴暗的。越近生命的尾声色彩越发灿烂、明朗。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他把握住了,明白了。他要把握的是什么?“某种虽为现实,却又是以激情画出的平和、悦人的东西。某种敏捷,综合,简练,集中,具有充分平静和纯粹和谐,像音节一般,给人以慰藉的东西。”这难道不正是一个画家活在世界上最现实的理由?难道他有把握的是有一天他的画可以卖一百万美元?劳动致富?这种希望是大街上大多数人的希望,不是诗人凡高的希望,如果画画的目的,仅仅是实现这种希望,那么为什么要画画呢?干许多事都会比画画更接近一百万。事实上这个希望一分钱都没有为凡高挣来。凡高也梦想着有一天他的画会卖掉,挣一大笔钱,他并不讨厌钱,事实上,在给提奥的信中,他不止一次提到把画卖掉的强烈愿望。但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恰恰是使画家一辈子渴望把画卖掉却一辈子受穷的原因,是的,他需要钱,但世界要付钱给他的是由于,此人对这个世界的审美力的蔑视,而不是他对它的审美力的迎合。我以为,凡高是幸福的人,因为他想做的他做到了,在他的画布上。因此,以为他的一生是所谓悲剧,只不过是一种媚俗,这是从如果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画就卖了一百万这一世俗假设出发的看法。然而,永远不会有如果,只有这一个在阿尔的天空下一意孤行的画者凡高。还是海德格尔的那句老话,他生下来,他画画,他死了。
后来在卢浮宫看到一副原作,画的是在阿尔的卧室。黄调子,辉煌无比。我在它面前坐了很久。这是凡高的家。如果从世俗的观点来看,这个家真是简陋无比,一张单人床、两把木椅子,一张小桌子,上面两个酒瓶,一个茶壶一个茶杯。我又一次听见了凡高的呼吸。某些观众如果意识到这是一个家的话,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不添些漂亮舒适的家具,或者内部装修一番。幸而他们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的家,而坚信他们面对的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作为物质的存在,这个家确实是相当简陋,但,它呈现的一切恰恰是对“简陋”一词的毁灭,这是一个多么丰富的家,只有一个有家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视觉和爱情。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具存在感的家之一,只有永恒可以在这里居住。凡高是幸福的人,他是一个有家的人啊。
我们在想什么?把这幅画买回去,为寒舍增辉。悲剧在我们中间,无家可归的是我们。有家的是凡高。
写于1997年秋天
来源:网络